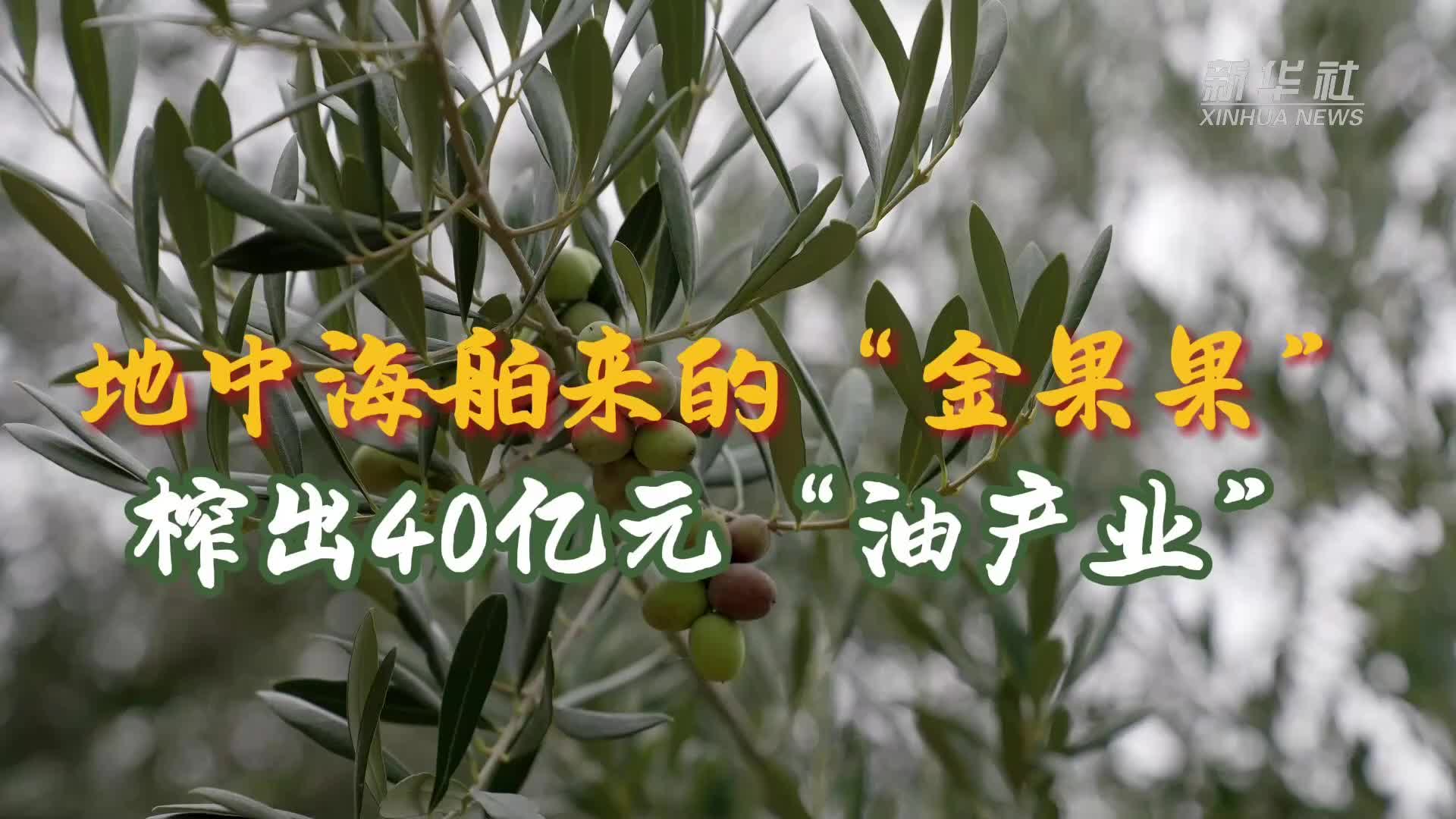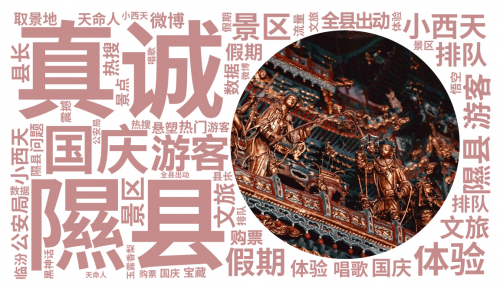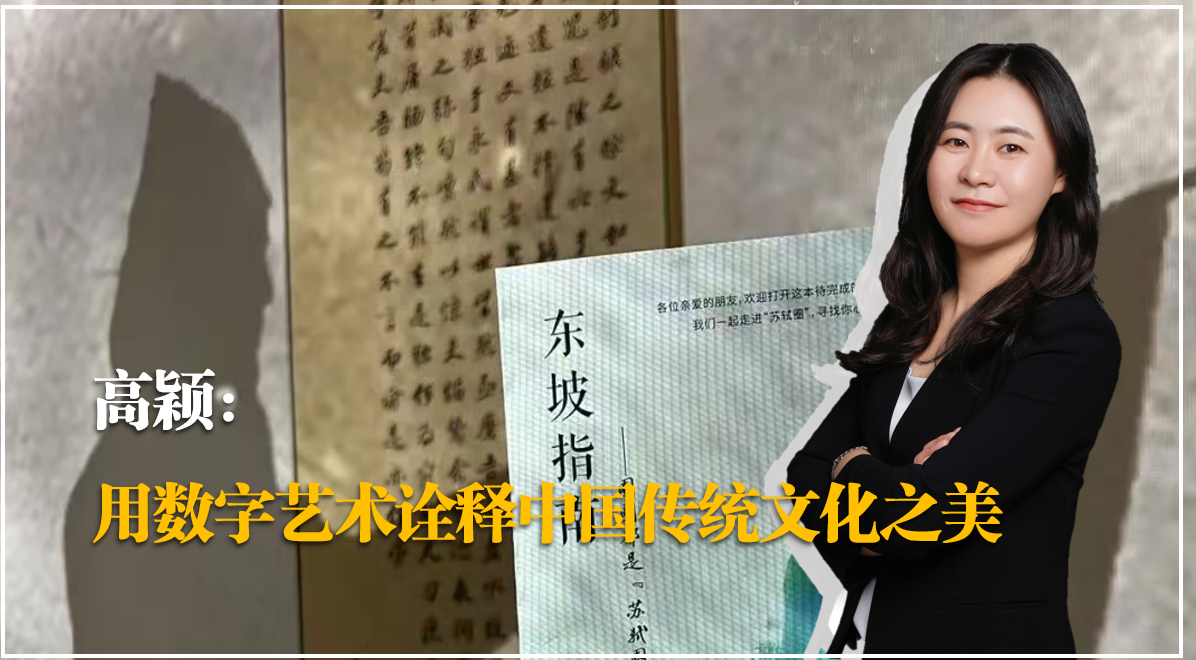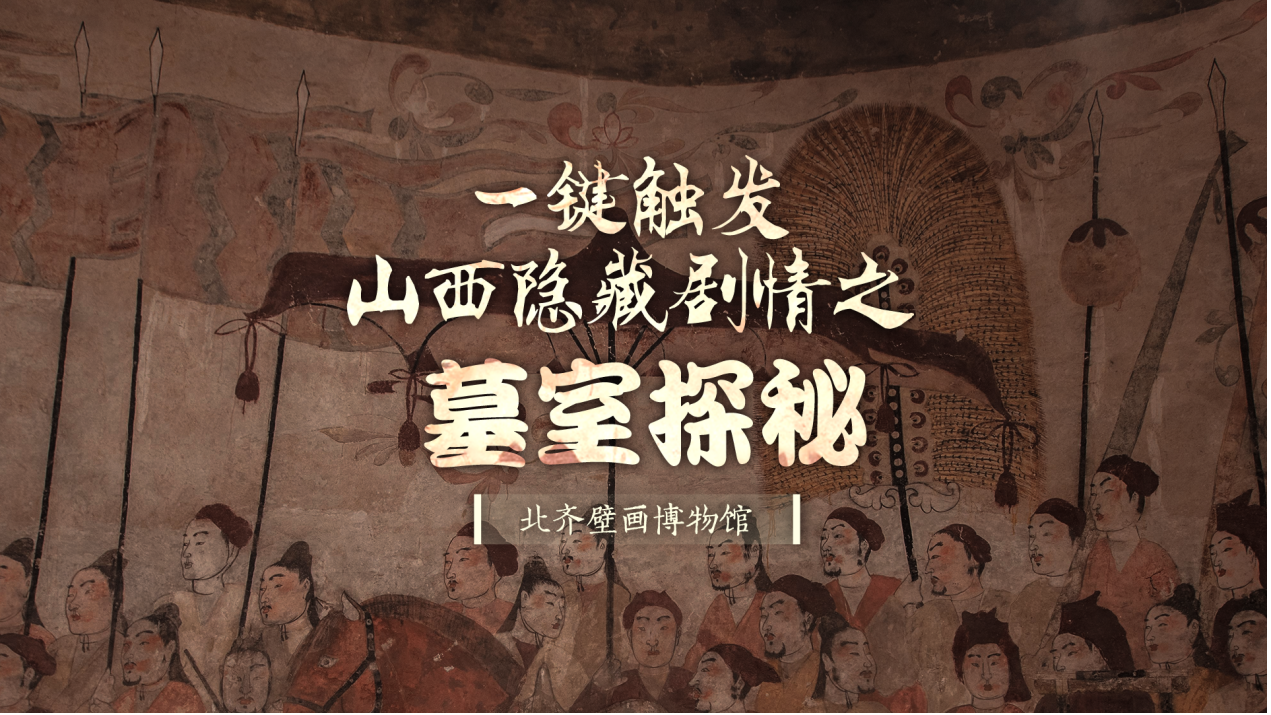消费文化下,舞蹈艺术走向市场化与消费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舞蹈艺术不仅应在经济层面注重活化产品,提高影响力、收益和价值,还应在文化层面更看重长远的传播效益和作品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舞蹈艺术向观众传递和传播的是编创者对生活的认知、思考及表达,舞蹈创作不应只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也不应是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只有打破传统的创作方式,关注更多文艺工作者的生存状态,贴近生活,汲取广袤的素材,才能将舞蹈艺术创作反馈到民间,为百姓带来更多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消费主义简述
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提到,真正的消费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逐渐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促进消费。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物资逐渐丰沃,催生出商品化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刺激消费。同样,市场也会采用商业性广告和宣传引导消费,以此形成大众较为成熟的消费观,对民众生活起到引导作用,从而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文化,这是属于费瑟斯通的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大众传媒观。
费瑟斯通借用作家布尔迪尔的重要观点指出,当前大众传媒蓬勃发展,呈现繁荣之势,使得消费主义得到发展;而消费主义的盛行则促使人们对商品的态度发生转变,即人们从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从重视商品的唯一实用性转变为回归日常生活中审美化。这些变化得到了商家、媒体、广告主的积极响应,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不断革新变化,创造新的代表性符号意义,使人们陷入消费文明中,消费欲望不断扩大,消费产品市场也不断扩大。
地域文化催生品牌,现代媒体有助于品牌的宣传与传播,也有助于引导消费。同时,品牌催生无形的资产,拓展品牌的衍生品,有助于刺激循环消费。舞蹈艺术正是需要循环消费以不断吸引更多的观众观看,并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在刺激大众审美心理的同时提高大众的审美认知。
舞蹈艺术“市场化”创作
“市场化创作”已成为当今舞蹈艺术创作体系中的重要表现,决定着当代舞蹈艺术的基本特征,舞蹈艺术的市场化、消费化趋势日益引人注目。
舞蹈创作中心由“作品”转向“观众”
当前,舞蹈艺术创作正从以“作品”为中心逐渐转向以“观众”为中心。近年来,舞蹈艺术作品的“质量”意识和“思想”意识不断提高,实质上是市场消费意识强化的结果,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观众”满意并为此买单。在消费文化影响下,舞蹈艺术创作者必然会更加关注“市场”和“产业”,舞蹈艺术走向市场化与消费化是一种必然。
大型民族舞蹈展演唤起的是消费大众在文化语境中对“民族记忆”“生存记忆”等久违的文化联想和审美满足,这一展演超越了消费社会中纯粹满足娱乐的大众文化产品,成为既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如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汇集了彝族、佤族、傣族、藏族、苗族、瑶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基诺族、景颇族、纳西族等12个少数民族及其众多支系的民族歌舞。符号的拼贴使云南各民族绚丽多彩的舞蹈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这种拼贴将不同艺术类型的符号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串符号意义”。民族舞蹈艺术展演作为符号表征,提供给消费大众的是符号消费,通常运用现代媒体的传播方式,将对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用于消费大众欣赏的拼贴和组合,使民族舞蹈艺术展演的符号叙事有更丰富的后现代意义。
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内在审美逻辑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符号的意义通过某种机制被组合在一起,能够像魔术师一般不可思议地制造出意义链条,满足人们无限的需求。”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观众”成为舞蹈艺术创作的中心。
中国著名编导周莉亚和韩真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从历史生产和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和元素,借助想象以及再现历史文化题材突出中华文化精神,彰显高度的文化自信。从《唐宫夜宴》《洛神水赋》到《只此青绿》,不断的“破圈”使其成为现象级作品,这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被当代观众所认可的,满足了观众的消费期待,更引领着观众的观赏习惯和审美方向。除此之外,还有英国舞蹈编导马修·伯恩的男版《天鹅湖》,对众所周知的经典舞剧进行创新,打破了以往芭蕾舞剧以女性为中心的范式,拓宽了人性命题,激发了观众的“期待视阈”,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舞蹈艺术不仅应在经济层面上注重活化产品,提高影响力、收益和价值,还应在文化层面上更看重长远的传播效益和作品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它向观众传播的是时代之声,而不是一时的名声大噪,这对大众而言是接受、理解和包容。
舞蹈创作题材由“传统题材”转向“现实题材”
舞蹈创作的题材不是随便寻找或凭空捏造的,而是编导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体现着编导对生活的认知以及其自身的一部分实践经验。广义的题材是指舞蹈艺术作品对某一生活范围的客观选择,如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军旅题材、农村题材等。狭义的题材是指作品中具体的生活现象,如王玫编创的作品《天鹅湖记》,她通过挖掘生活现象背后的内涵进行题材选择,将夸张化的“搬腿”动作及大量假肢搬上舞台,幽默中夹叙着大量反讽修辞,抨击层出不穷的舞蹈比赛过分强调舞蹈演员“职业化”的畸形发展现象,并对当前的艺术教育现象进行反思。舞蹈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舞蹈创作的素材,从素材到题材的选择体现的是编创者对生活的认知、思考及表达。
当前,舞蹈艺术的题材正由传统题材向改编题材和现实题材转变。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当今舞蹈艺术的观众“期待”成为影响舞蹈艺术题材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准则和社会历史进程等各个因素都影响着舞蹈艺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舞的发展。其进程十分缓慢,原因在于舞蹈拓荒者吴晓邦在学习西方现代舞后谋求在中国大地上走出一条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艺术创作中进一步挣脱传统习俗的束缚,但却遭到“资产阶级的现代舞、文艺思想不对头”的蛮横指责。从弘扬主旋律的军旅题材到更大胆地进入精神世界,自由地表达历史与现实人生问题的个人思考,再到中国现代舞进入本土整合期,中国现代舞的创作模式、审美原则均有了新的突破,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期待,使观众的审美心理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
舞蹈艺术创作往往会选择观众广为熟知的传统题材,在此基础上改编或重新编创的作品具有创新性,十分吸引观众的眼球。如改编自文学名著或小说的作品艾夫曼的现代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王玫的现代舞剧《雷和雨》和《洛神赋》、张艺谋执导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王媛媛的现代舞剧《惊梦》、肖苏华《梦红楼》等,根据音乐改编的舞剧《春之祭》《波莱罗》《我们看到了河岸》等,编导选择别人的材,借题发挥,表自己的意,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
舞蹈表演者用肢体语言表现舞蹈艺术的魅力,擅于抒情、拙于叙事,其在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方面极具难度。在表现生活内容方面,特别是现实主义题材,容易陷入讲故事的诟病或流于表象。如果现实题材的编创只选择了现实题材的时间,没有选择该时间内所展示的精神内涵,那就是一个伪现实题材。在舞蹈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好与坏取决于编创者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在题材选择中,舞蹈编导做得好就是“好材物尽其用”,做得不好就是“坏材暴殄天物”,而这一结果与编导的个人表达,即作品的立意有直接联系,当立意有高度时,该作品就是有意义的。一个舞蹈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不仅要从作品的立意层次上分析和评判,更要从社会角度看其是否具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舞蹈创作从“传统题材”走向“现实题材”是必然趋势。舞蹈编导需要关注不同艺术门类间的交叉互融,拓宽思维,深入探究方法论。只有打破其原有的思维定势,并接受新事物,进行新思考和新行动,才能通过悟性不断构建出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在舞蹈创作中,如果没有好的内容与形式,再好的创意也乏陈无味;而对“走心”的内容来说,即使只是只言片语,也必能直达人心,引起观众的共鸣。只有从人的属性出发探索真实情感,从生活现象中探索本质,才能找到对人性和情感的感悟,对时间和生命的态度,以及人文关怀,最终找到创作“现实题材”的内涵。
舞蹈创作方式由“体制内创作”转向“体制外创作”
“体制内创作”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地方级的歌舞团或学校里的歌舞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带动了艺术的产业化,这为舞蹈艺术提供了更多创作空间,因而也涌现了一群进行“体制外创作”舞蹈艺术的自由创作者。“体制外创作”是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创作,主要指舞蹈艺术的官方活动之外的创作,是一种“自由”的创作方式。目前涌现的沈伟、戴剑等著名编导,以及谢欣舞蹈剧场、侯莹舞蹈剧场、广东现代舞团、陶身体剧场、鹰剧场、上海金星现代舞团和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舞蹈编导和演员。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在生活和创作上面临着现实困难和瓶颈,应加强对体制外文艺工作者的各方面支持,更加关注和关心新的艺术群体、体制外文艺工作者的生存状态。
玛莎·格莱姆说:“‘舞蹈是发现,发现,发现!’那么,通过作品所找寻的是什么?通过创作,我们发现了什么?舞蹈实践提供了什么?我实现了什么?确实,一个编导的真实就是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编舞的‘人’——‘你是谁?’”2014年,中国舞协主办“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为更多成熟的自由舞者和编舞者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广阔的创作空间。除此之外,还有“北京舞蹈双周”和“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等舞蹈周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舞者和编舞者共赴舞蹈佳作盛宴,为观众带来不同的体验。
文化消费下舞蹈创作回归身体原点
舞蹈艺术“市场化”创作中的身体消费
在消费主义时代,技术变革,物质兴起,人们对物质的消费欲望更多是通过精神来呈现的,大家所谓的购买是精神而非物质。同样,身体在消费主义时代充当着消费品,牵制着人们的审美体验,更多的是给予人们感官上的愉悦和享受。正如现象学创建者——胡塞尔提出的“回到事物本身”,人们应回到事物本质去观察身体,观察舞蹈艺术,而不是消费身体,消费舞蹈艺术,遗忘符号背后的文化生态。
21世纪,人们普遍存在焦虑,随着社会发展,身心分离越来越严重。吴海清在《身体在世性:被舞蹈批评遗忘的起点——现象学视野中的舞蹈批评之反思》一文中提出:“身体在世性就是身体与世界互动、遭遇的自我。”一方面,人不可能完全隔离于世,另一方面,人不可能完全被世俗淹没。世界是具有包容性的,只有在包容性的环境里人们才会充分发挥其创造力。身体也是如此,身体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与世界对话,又因发挥着它不可同化的独特性、主体性作用而在世。在艺术发展历程中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物质因素高于精神因素,比如在路易十四的《王后的喜芭蕾》中,身体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产物,从古典主义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精神因素多于物质因素,身体对自由的追求使其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工具。即使身体有着不可控性和可能性,但其本质都被哲学、宗教、政治、神话等文明的武器压制着。舞蹈虽以身体为载体,但正是身体的象征意义使得舞蹈成为象征性舞蹈,也正是因为舞蹈的象征性使其忘记身体的本来面貌。身体作为舞蹈的载体,应该发挥其主体性作用,与世界对话。
舞蹈创作回归身体主体性和生活
如果说舞蹈作品创作是编导的一度创作,演员是二度创作,那么观众则是三度创作。三度创作可以超越舞蹈范畴,如将哲学、科学、宗教、伦理和历史等精神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融入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作为审美主体,我们能够通过身体看到舞蹈作品所传递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看到时代发展的进程和人类的思想进阶,同时也不应局限于精神性范畴或技术性的身体而脱离舞蹈范畴。
消费文化下,舞蹈艺术走向市场化与消费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应该保有创作者该有的真诚以及对待舞蹈艺术热忱的态度。舞蹈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正如朱光潜所说:“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懂生活的人是艺术家,他的人生就是艺术作品。”生活和艺术本为一体,舞蹈艺术应融于群众的生活中,为群众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慧娇.民族舞蹈舞台展演文本的符号叙事[J].艺术教育,2019(10):261-262.
[2]许锐.传承与变异、互动与创新[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
[3]吴海清.身体在世性:被舞蹈批评遗忘的起点——现象学视野中舞蹈批评之反思[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5(01):37-40.
[4]赵书峰.原生民俗性与舞台审美性——“云南省第十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观后感[J].人民音乐,2019(03):42-45.
[5]赵书峰.文化非本质主义·主体性·自我民族志——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观念[J].星海音乐学报,2020(02):59-66.
[6]郑佳丽.浅谈接触即兴的训练价值[J].艺术大观,2019(26):2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