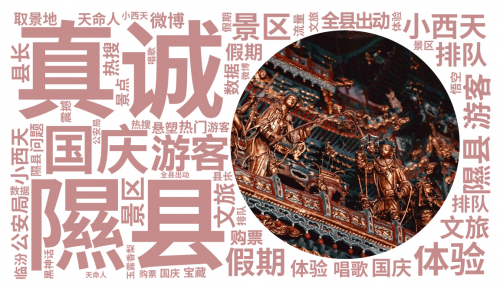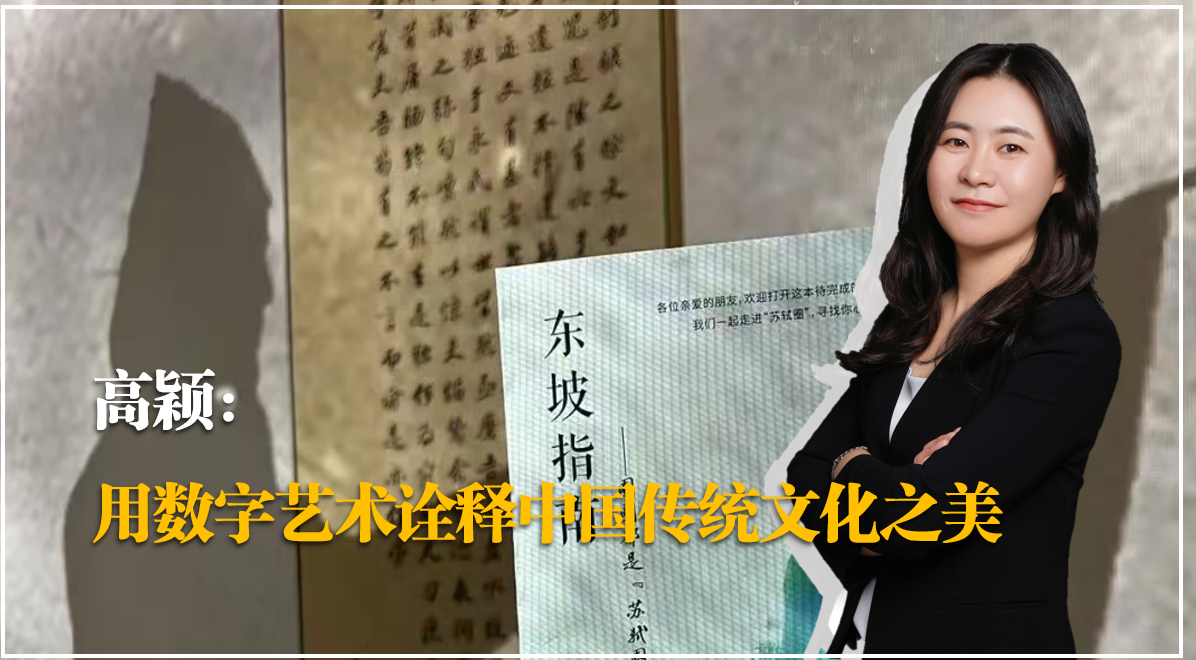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蚕桑”作为文创产品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是诸多文创产品的灵感来源和实践载体,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以“蚕桑”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却存在产品同质化、低质化、模式化和“符号表面化”等问题。为实现“蚕桑”文创产品的涅槃重生,将“蚕桑”文创产品纳入设计伦理视域,重新思考,重新发掘,迫在眉睫。基于此,“蚕桑”文创产品需要找到自己的重构之路,不断追求“器”的完美和“道”的完美,在“道器”之间实现从“次性化”向“可持续化”的转变,从“静态”产品向“动态”形式的演变,从而使“蚕桑”文创产品实现再次辉煌。
“蚕桑”作为文化符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交流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是汉代的“丝绸之路”,还是现今的“一带一路”,蚕桑的商品意义和文化标本意义都从未有过改变。就文创产品而言,“蚕桑”母题效应更是被大多数文创人津津乐道。无论是来自故宫或敦煌研究院等设计院所的设计师,还是平凡的设计人,都对“蚕桑”的文创设计情有独钟。可以说,“蚕桑”文创设计具有全民性和普遍性。
在如此繁荣的局面下,难免会出现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特别是“蚕桑”文创产品中出现的设计伦理偏差,更是让人惋惜。鉴于此,笔者以敦煌博物馆线上商城中的“蚕桑”文创产品为主要切入点,探索目前“蚕桑”文创产品的样态、存在问题以及突破路径。
特征与问题:“蚕桑”文创产品的现实状况
笔者将敦煌博物馆线上商城中的“蚕桑”文创产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敦煌博物馆线上商城中的“蚕桑”文创产品较好地兼顾了文创产品的艺术性和市场需求。且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敦煌博物馆线上商城中的“蚕桑”文创产品本身的特点较为突出,适合成为研究的“标本”。其特点如下。
其一,“蚕桑”文创产品具有系列化特征。产品系列化的设计分类方式可以让主题鲜明统一,有助于更好地、多方位地挖掘品牌特色。敦煌博物馆线上商城中的产品分为多个系列,包括再创敦煌(15件)、飞天(23件)、佛系(15件)、伎乐天(24件)、九色鹿(23件)、纹样(16件)、极乐(15件)等。“蚕桑”系列故事和特色元素符号,不仅丰富了整个线上商城的整体框架,还满足了消费者的爱好需求。
其二,“蚕桑”文创产品包装样式视觉体系化。包装不仅可以很好地体现产品的文化内涵,还可以给予消费者同等的文化附加等级,同时,其也是商家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创产品的包装是促进文创产品市场化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蚕桑”文创产品包装赋予了“蚕桑”文创产品个性化的时代需求,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更有活力。
其三,“蚕桑”文创产品的文化内涵挖掘日趋符号化。“符号化”是“蚕桑”文创产品的重要表征,更是体现其市场区别度的重要内容。现阶段文创的设计路径就是在挖掘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找到其独具特色的符号语言,用艺术的手法提炼整合,形成文创产品。如敦煌博物馆线上商城中销售的九色鹿帆布包和祈福御守(图1),是以敦煌第257号洞窟西壁中部北魏时期的《九色鹿经图》(图2)为符号元素,取其祥瑞灵兽的寓意,经提取整合而创制的文创产品。


事实上,敦煌博物馆线上商城是极为成功的文创产品销售商城,然而在看到其成绩的同时,也需要发现“蚕桑”文创产品所存在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从文创的行业角度来说,这几乎是行业问题,而从设计伦理角度来说,这也是设计在伦理方面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其一,文创产品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导致“文化资源”过剩。在浏览各种线上和线下的文创平台时不难发现,各类形式差别不大的文创产品充斥着整个行业。如继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朕知道了”手账胶带纸出现后,各大博物馆和品牌商推出了各种不同纹样的胶带纸。事实上,各式各样的文创形制载体被推出,进而大批模仿者进行模仿复制,才是文创产品走向同质化的原因。这一过程会导致一部分文创产品成为过剩的“文化资源”,造成资源浪费。
其二,文创产品低质化趋向严重,导致生态压力过大。在资本和利益的驱动下,为了降低文创设计产品在材质方面和其他环节的成本,文创产品在近几年被打上了“文创=低质”的烙印。甚至,部分设计产品因可降解度不够,被丢弃时对自然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事实上,这是需要市场、商人和设计师共同考虑的问题。
其三,文创产品模式化日益严重,导致创新力不足。中国人发明了以标准化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即模件化体系[1],例如通过基本的笔画,依照简单的数学原理建立系统,构成了汉字。现在的文创产业片面地沿承了这种方式——新的创造载体被创造出来后,通过载体形式的复制,改变画面或者一些部件即可成为新的文创产品被销售。越来越多的设计从业者也被迫通过简单培训,按照文创产品圈形成的既定模式进行设计生产,然而,这不是效率的提升,而是创新机制的缺乏以及同质化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
其四,文创产品可视化元素的提取过于“符号”和“表面化”,造成过于表象化的消费。人的意识思维过程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是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和再生的操作过程[2],设计的过程也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可视化的“符号”经过设计师单方面的提取整合为产品后,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交流直至被认可,就是一种符号的被动接受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是设计的被动接受者。在研发前期,开发者充分参与,同时迎合消费者“符号化”的消费欲望,对具有“本真性”的文化符号的提取则点到为止,从而使得文化的内在精神被简单表象化,也引导消费者走向了一种表象化的产品消费。所以,消费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致大多来源于当代社会生活中可以刺激到他们的有趣的“新”符号。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不再是“过去”的代名词,而是“新的符号”的重现[3]。
其五,文创产品使善化缺失,导致伦理的问题出现。在今天,盲盒的出现,让许多年轻人和消费者进入了巴赫金所认为的“第二种生活形式”中,即他们放下了真实世界,在看似因兴趣而缔造的共同体中交往,建立虚幻的世界,彼此相互认同,彰显个性,使自己进入无边的虚空世界[4]。更为可怕的是,盲盒不再仅以“静态”的形式出现,甚至宠物也开始出现在盲盒产品中。在运输和被收养的过程中,宠物偶尔会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也是设计导致的伦理问题的表现。
道器转化:“蚕桑”文创产品的内在重构之路
针对前文所提及的“蚕桑”文创产品中存在的“五大问题”,其破解方式乃是“设计伦理”,即在“蚕桑”文创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增加“伦理环节”,并将“伦理环节”与“设计环节”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将两者视为同等重要。也就是说,在“蚕桑”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既要追求“器”的完美,又要追求“道”的完美,而且在“道器之间”需要投入更多精力,要实现“次性化”向“可持续化”的转变和“静态”产品向“动态”形式的演变。其具体重构路径如下。
其一,“蚕桑”文创产品设计要从“器”的完美向“道”的完美进阶。所谓“器”的完美,就是要更好地理解“器”的概念。所谓“器”,就是我们所设计的“实体产品”。维克多·帕帕奈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曾说过,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应平衡市场中的各个要素环节,对设计所解决的问题和质量负责。设计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创造更为幸福的生活,而幸福是与道德相对应的现实活动,是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的善,即至善[5],所以由此可见,设计符合“至善”的伦理要求,所以“器”的完美所带来的“至善”效应,也必将使更多人在生活中获得幸福感。所谓“器”的完美就是将“至善”“幸福”等核心理念最大化。所谓“道”的完美,就是文创产品设计过程中人文精神和道德归属的最大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道”需要框定为设计从业者和设计行业的意义在世界共同体中的批判性而演变出的以价值观为分析前提的“道”,这里所提到的是人文精神、道德归属等。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针对机械化运作导致大众福祉的缺失,提出“人类完美”是文化发展之终极目标,它应是人性等各方面的和谐完美,是社会各部分达到的普遍完美[6]。从“器”的完美到“道”的完美的进阶,也是向“人类完美”的进阶,是开始强调人文精神、道德准则的变化,这也使得文创设计的道路有了内涵及意义上的深化,这也是对伦理价值的回归。
与此同时,在“道器之间”还需要加强制度伦理、政策的约束。法律是促进善德的永久制度[7],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基础,有利于道德伦理的建设。以法律对文化资本运作中的价值进行有效的规制约束,对资本进行正确的引导,完善文创市场道德体制、法规的建立,更需要完善文化创意产品及商人的制度伦理规范。在“设计伦理”的视域下,法律、商人、文创产业从业人员是缺一不可的“伦理闭环”。法律制定者是文创市场的保障和基础,商人是文化市场的活跃要素,文创产业从业人员是文创市场的输出者。在“设计伦理”的视野下,他们都需要进行全方位的道德完善,重构心理秩序,只有这样,文创设计的“道器转换”,或者说“有器而道”的进阶,才有现实意义的可能和可实现化的路径。
其二,“蚕桑”文创产品设计要从“次性化”向“可持续化”转变。模件化体系在中国的艺术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模件化会或多或少导致同质化,但是中国的艺术一直没有受到过多的这种阻碍。南朝陈画评家姚最在他的《续画品》中提到:“学穷性表,心师造化。”正是中国的伦理中顺应自然法则的观念,才构成了中国艺术的可持续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自然造物,应是至善境界。对于过剩的文创产品,我们或许可以借鉴“共享经济”的概念,即分享者通过分享他人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通过共享经济,我们或许可以构建一个交换的平台,不仅通过闲置资源的二次交换形成新的经济点,也有效遏制过剩的文创产品被再次生产。
其三,“蚕桑”文创产品设计要从“静态”产品向“动态”形式演变。或许,在景区中我们经常会在年画、糖人等手艺人面前驻足观看,甚至因留恋而不愿离开。随着一些景区中非遗传承人、手艺人的现场演示的出现,游客不由自主地被这些手工艺产品和非遗产品吸引。在这个过程中,游客是自主地被文化所吸引,同时,此时的文化带有较多的“本真性”。对此,我们不妨利用这个带有较多“本真性”的环节,让部分“静态”的产品,部分演变为“动态”的形式,即由消费者自行参与设计环节。在体验和理解了“本真性”之后,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能使消费者自主参与文创设计的环节,从而使文创产品在形式上得到转变。
综上所述,笔者从“设计伦理”出发,在分析目前“蚕桑”文创产品的现状与“五大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蚕桑”文创产品重构的“三大实现路径”。这是笔者对“蚕桑”文创产品设计的思考,但是这类思考仍然存在局限性。同时,虽然笔者的针对对象是“蚕桑”文创产品,但是对其他文创产品设计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这也是笔者在以后的文章中的发轫点和关注点。与此同时,对“设计伦理”而言,将“设计伦理”应用于具体的文创产品,其实是为“设计伦理”找到了落脚点,这也将是“设计伦理”研究的另一面向。在实践中展开“设计伦理”研究,不断完善“设计伦理”的理论和实践,也将是笔者孜孜以求的学术道路。谨以此文,抛砖引玉,以期学界更多有识之士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设计伦理”和“蚕桑文创”之上,让两者之研究更为深入和普遍。
参考文献
[1]雷德候.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M].张总,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2]马克斯·本泽,伊丽莎白·瓦尔特.广义符号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蒋原伦.传统的界限:符号、话语与民族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115-121.
[5]田海平.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J].道德与文明,2014(03):26-32.
[6]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