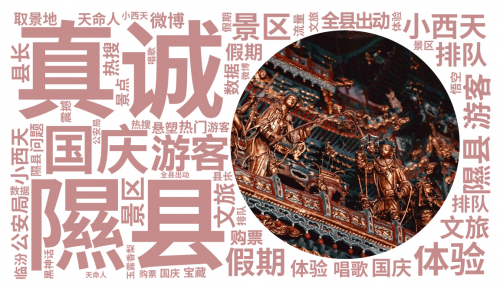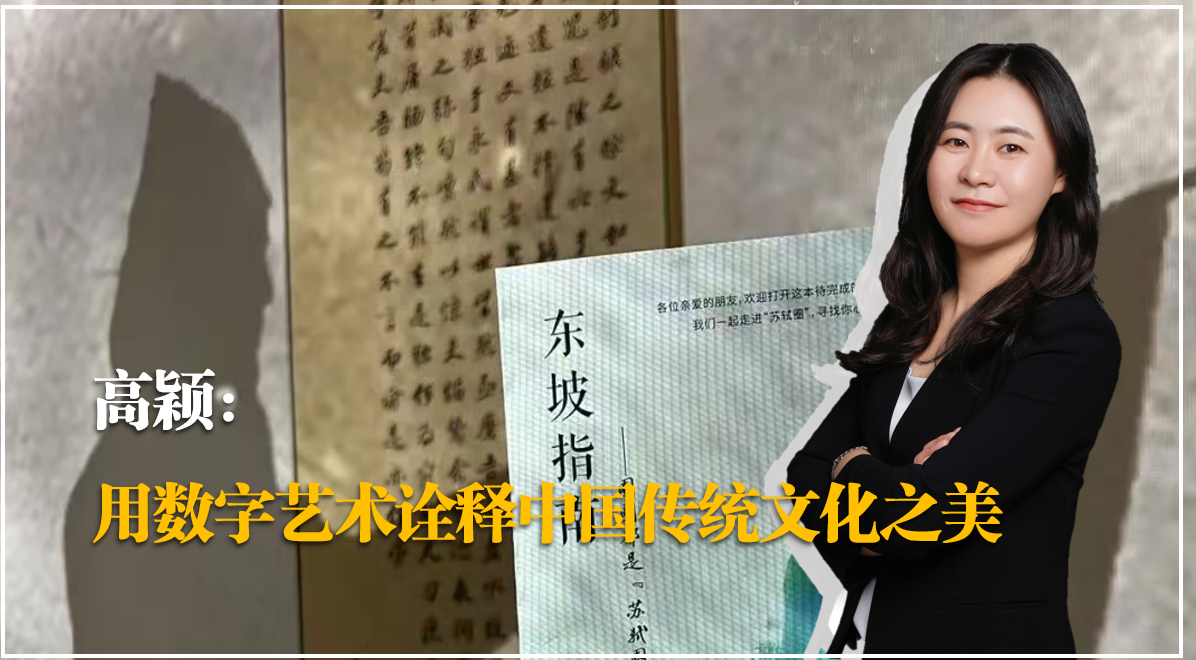楚国的青铜器最能彰显出贵族的风度,体现社会流行风尚。通过对西南丝绸之路的青铜器与西北丝绸之路的青铜器进行对比,揭示楚人探索西南与西北丝绸之路的民间商贸之道。“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应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不断加大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力度。
关于楚文化的研究材料特别丰富。从材料类型来看,有考古发掘报告,出土器物和大量相关文献等。而从考古发掘报告可知,器物材料、器物图像和丝绸是重点。通过器物图案的描绘、丝绸的传播,可判断楚国形成丝绸之路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多样化、高品位文化需求的重要基础,也是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以纪南城为核心的楚墓群出土器物来探讨楚国丝绸之路的形成。
据文献记载,在楚国8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建有丹阳、郢、鄀、鄢、陈、矩阳、寿春等8座都城。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从丹阳迁都至郢,至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公元前241年,楚都东迁于寿春。“郢”字最早出现在春秋初期,《世本·居篇》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
据文献与论文研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以纪南城为中心的江汉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符合“依山傍水”选址原则。
张正明教授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存在,东起长江中游“郢都”(今湖北的江陵),西至恒河中游的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纳附近),途经长沙、贵阳、昆明、缅甸等地,中间要越过横断山脉。
楚国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探索
2013年9月7日、10月3日,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按照路线走向,分为北方、南方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三部分,南方丝绸之路可细分为西南丝绸之路与岭南丝绸之路。
(一)楚国青铜器在西南巴蜀的流传与影响
楚国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精神、科学技术和风土人情,楚国青铜器是楚文化的重要载体。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指出:“中国青铜文化自身的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它不是由域外传来的,而是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而中国青铜文化起源的本土论并不排斥其起源的多元论……西周后期至春秋末年,中原文化对外影响进一步扩大,促使原来中原周围地区的一些青铜文化逐步融入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统一青铜文化体系,而在这一文化体系内部,由于政治上分化趋势的加强,导致东周时期出现了周郑晋卫、齐鲁、燕、秦、楚与吴越六个文化亚区。”此前楚地是著名的先民聚集地,这里有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城头山遗址、大溪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楚文化的起源地主要分布范围包括今湖北全省、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和安徽西部。楚纪南故城处于湖北江陵地区东周楚文化遗址分布区,在这里出土了最能彰显贵族风度的青铜器。考古学家将青铜器的生产与运用作为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并称当时社会为青铜时代。
楚国青铜器纹样与巴蜀青铜器纹样类比简析
刘彬徽先生在《楚系青铜器研究》中,首次全面系统地收集了楚国青铜器的资料,对其进行了分期,并从器物的组合及形制方面探讨了楚国青铜器的特征。楚系青铜礼器一般指东周时期楚国及其附属国出土的、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青铜礼器。
楚文化青铜器的纹样分为三大类:龙凤纹、几何纹和其他物象类。楚人崇尚凤图腾,因为楚人的祖先是南方神祝融,他是凤鸟的化身。凤是楚国崇拜的神灵。而巴蜀的青铜图腾纹样主要是蛇。余云华《重庆文化主源头:来自伏羲族的“蛇”巴》一书中指出,重庆是最初被称为“巴国”的地方。《说文解字》:“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巴为图腾名、族名、地名,是“蛇”的意思。重庆的下层文明是由巴人所创,他们的祖先以蛇为图腾。后来,一群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回到了巴渝,他们的祖先也是伏羲,但“虎巴”是在“蛇巴”之后才出现的,因此,重庆的主体和基础就是蛇巴。在1960年5月湖北荆门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兵辟太岁”戈,据荆州博物馆的资料介绍:“通长21.9、内长8、宽6.5厘米。宽直援,前锋尖锐。援两面各铸一神人,头上插羽,双耳珥蛇,睨缠两蛇。”曾占有当时天下之半的楚国,民族文化交流政策较为开明,文化繁荣,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文化系统。从战国时期开始,楚与巴蜀进行了深度的文化与贸易交流。
西南丝绸之路的雏形
有资料显示,夏商文化传入四川,形成了古代蜀地的文化。春秋时期,秦、楚两国的崛起,切断了蜀地与中原的交流,致使其文化发展陷入了停滞状态。而在战国早期和中期,古蜀文化再次繁荣。秦灭蜀后,蜀文化逐渐衰弱。到了汉代,蜀文化逐步被汉文化所替代。
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有三个条件:其一,古代楚与蜀从三星堆遗址的早蜀文化和石家河遗址的先楚文化时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其二,双方的战争和人口迁移也是楚与蜀文化的载体;其三,古代楚人进入西南地区的两条道路为汉中大巴山线路和川江线路,交通畅达。
方国瑜先生从楚墓“料珠两件”中推测,西南丝绸之路源于印度的蜀身毒道,最晚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了。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还提到“蜀身毒道”,即从公元前2世纪起,这条路线就与长安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共存,这条路线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晋时期,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印交通要道。季羡林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大陆的丝绸最初是由云贵地区传至印度,再由滇缅的渠道进入。”一条完整的通道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发展,而在这条道路成型之前,就已经有了便利的运输系统,特别是在村庄的运输系统。当道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农村道路就会变成一条商业之路,而在官府投资的情况下,便会成为官道。南方的丝路不仅是一条民间的贸易通道,也是使节、朝贡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纽带。“西南丝路”即南丝路的“西线”,是从四川成都经过云南到缅甸,再向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中海一带的“蜀身毒道”。
(二)楚国丝绸技术的成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系统成型的源头之一。1965年,江陵望山1、2号墓出土了花卉纹绢绣、动物花卉纹绢绣和石字菱纹锦绣。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出30多件丝织品,这充分展示了当时楚国高超的丝绸工艺水平。1987考古发掘包山楚墓,其属于战国中晚期古墓,当时正是楚文化由鼎盛时期转向衰落期的阶段。1981年江陵九店砖厂楚墓乙组墓出土17件丝织物和麻织物,多件是龙凤纹刺绣或者凤鸟花卉纹刺绣。
最初,楚国的丝绸生产与青铜兵器的铸造一样,技术水平较低,而当时鲁国的丝织技术非常先进,为了得到鲁国的丝绸技术,楚国以武力威胁鲁国,逼迫鲁国用数以百计的技术工匠来换取短暂的和平,掘到了发展丝织业的“第一桶金”。正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楚国大兵压境,准备侵入鲁国的阳桥,孟鲁孙贿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后来,楚国将这些工匠都安置在楚国国都纪南城的王府手工业区,从事楚国的丝织业。楚国的对外扩张旨在不遗余力地谋求发展本国的纺织业,无论是资源还是技术,都尽可能占为己有。
楚国对西北丝绸之路的探索
(一)西北丝绸之路的起源
大量的文史资料显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丝织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当时,最为发达的是中原之地,史有“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之说。但是,考古发掘出土这一时期的丝绸实物,却几乎都发生在楚地,尤其是以湖南长沙市郊和湖北荆州最多。夏商时期,是我国历史跨入文明门槛后的第一大发展期,纺织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丝绸业的生产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比较复杂的手工织机和高超的织造工艺。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马山一号楚墓的考古发掘,印证了楚国的丝织业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纺织技术水平。
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2号墓的《人骑骆驼铜灯》,由豆形灯与人骑驼形灯座两部分组成:灯盘较大,平沿稍内敛,厚方唇,浅腹,盘内中心有一尖形烛针,高1.6厘米;腹外壁呈瓦纹内收,灯柄较长,近盘处较粗,中腰与下端有凸箍,柄尾则插入铜人手捧的铜圈内,与灯座连成一体。铜人扬起头,端正地坐在骆驼背上,目视前方,圆滚型脸庞,双手弯曲,双手撑在圆筒状的铜环上,支撑着灯杆,两膝盖弯曲,脚尖抵在骆驼身体的两边;驼首向前,脊椎弯曲,四足立在一块长方形的青铜上。灯座之人与驼为分别铸制,然后用铅锡合金焊接为一体。通高19.2厘米,灯盘径8.8厘米。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推测其制作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与荆门包山楚墓为同一时期。因此,骆驼的出现代表楚人探索过西北沙漠。也就是说,在战国中晚期,楚人探索西北的同时也将丝绸带到了那里。
(二)西北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神秘的楼兰,当年曾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是中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西汉时期,这里曾“设都护、置军候、开井渠、屯田积谷”,总人口一度达到1万4千多人,商旅云集,市场繁荣,成为中原文明在西域的一个张力点。从古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在公元2世纪前,楼兰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
“一带一路”民族融合的文明借鉴之路
楚国在扩大疆域的过程中,重新组合了区域的整体结构,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的楚国是通过“蜀身毒道”完成对西南丝绸之路的探索的。
西南丝绸之路是不同时期云南与四川、西藏等地区对外连接的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丝绸、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以及与内地的物资交易,从而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格局。
西北丝绸之路的畅通带来了丝路东西方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当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东传进入中国时,融合了希腊文化的犍陀罗艺术也随之而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与实施,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日益密切。“一带一路”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沟通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助推国家形象建构步入了互联互通的新阶段。作为承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也是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具体实践工作时,应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持续推进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既要注重不同国家、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又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两廊一圈”“琥珀之路”“光明之路”等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基本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也是我国展现开放自信、和平发展形象的重要机遇。
参考文献[1]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01):84-97.
[2]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J].史学集刊,1990(03):12-23.
[3]张正明.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J].江汉论坛,1990(04):71-76.
[4]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5]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6]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J].江汉考古,1983(01):1-18+50.
[7]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8]刘玉堂.楚国经济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9.
[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铜绿山考古印象[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10]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的考古学考察[J].江汉考古,2012(02):85-92.
[11]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1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3]张莉清.东周楚国高级贵族墓地制度探研[D].武汉:武汉大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