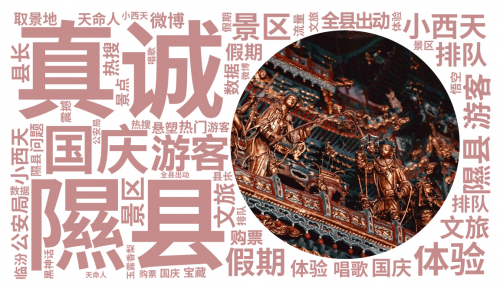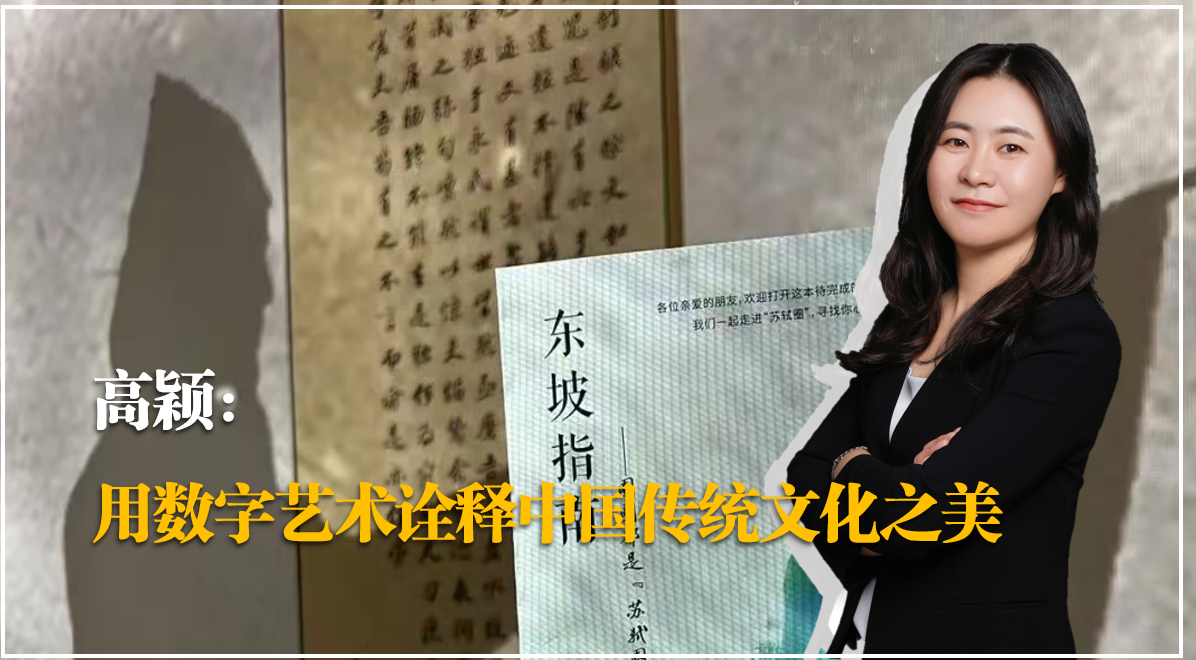狭义的“电影作者论”指的是法国色彩鲜明的电影实践及批评理论。1951年,著名电影批评理论杂志《电影手册》创刊,《电影手册》以“导演即作者”作为创刊主题,特吕弗顺延“用光写作”这一理念的发展历史,并延伸了其文化逻辑,向世界正式提出了系统的“电影作者论”。现尝试拓宽研究视域,探讨如何通过电影中电影装置的再媒介化创作作者电影,凸显电影作为大众最常接触的艺术种类所蕴含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品位。
“电影作者论”与作者电影的诞生
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三剑客”之一的弗朗索瓦·特吕弗提出了“电影作者论”(Auteurism)这个名词,这一定义诞生之初直接与法国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法国本土或欧洲艺术电影的传统与实践相联系,因此狭义的“电影作者论”指的是法国色彩鲜明的电影实践及批评理论。但当我们投入世界电影理论史的长河之中,“电影作者论”的倡导与实践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历史渊源。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于1943年指出“电影的价值来自作者”,这种观念是将电影导演放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将导演视为文学作品的作者。作为这一创作理念的延伸与发展,法国导演阿斯·特吕克在1948年提出了“摄影机—自来水笔”的著名主张:执掌摄影机的导演应该像创作文学作品的执笔者那样自由地书写叙事。1951年,著名电影批评理论杂志《电影手册》创刊,《电影手册》以“导演即作者”作为创刊主题,鲍德·威尔在杂志上发表了以此为主题进行论述的文章《作者策略》,使得“电影作者论”这一理论从此对非好莱坞艺术电影的创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吕弗顺延“用光写作”这一理念的发展历史,并延伸了其文化逻辑,正式提出了系统的“电影作者论”。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作者论”在诞生至往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主流商业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进行分庭抗礼的一种艺术电影实践指导及批评理论。“电影作者论”是特吕弗以好莱坞著名导演希区柯克的作品为研究文本进行总结提炼后得出的。它在成为对世界艺术电影的一种自我命名方式的同时,也成了希区柯克这位被特吕弗赞为“世界上第一位电影作者”的伟大导演的诞生标识。在此,笔者引用其广义的定义,探讨如何通过电影之中电影装置的再媒介化创作作者电影,凸显电影作为大众最常接触的艺术种类所蕴含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品位。
电影中的电影装置:电影的再媒介化
“装置”(Installation)一词可以引申为“装配、组合”。现代艺术实践中流行的“装置艺术”(The Art of Installation)则是指将现成物品通过错置、悬空、分割、集合、叠加等手法,置放于新的展示场所,重新建构物体本身的意义。作为表现元素的物体、物体所在的展示环境以及实物的正常呈现这三个元素构成了装置艺术的意义界域。依照特吕弗的观点,“作者电影”需要向观众展示出电影作者/电影导演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风格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标识,它不仅要求导演在个人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甚至鼓励导演以自己的方式在作品中留下“签名”。其中,最显著的创作标识莫过于导演在电影之中通过视听语言向观众展示自己内心的电影本体。这一标识既是电影导演独特的创作痕迹的浓缩,也是其观看世界的独特视角与观众视点的重叠,而这一标识出现在电影创作之中,显征往往就是在电影中出现电影或者电影标志的装置。电影作者/导演通过在电影中搭建象征电影拍摄元素的影像装置,或是直接将经典电影摄入镜头之中,将电影“再媒介化”(Remediation),将“电影装置”的隐喻转变为电影的一部分,构建出媒介性组织框架,使装置中的电影与叙事本身生成同构关系,电影与摄入其中的影像装置导致观众观看视点的重叠,并通过叙事序列的叠加制造出可供阐释的多重语境。
电影作者以这种更为内敛含蓄的方式向观影群体展示属于自己的作品标签——电影本体的多样化,个人风格的烙印毫无痕迹地隐藏在了电影的叙事之中。蔡明亮的《是梦》以主人公“我”的童年回忆出发,“我”与外婆来到影院看电影,镜头却一直背对银幕,拍摄外婆与情人的特写。坐在前排给情人喂食糖水凤梨的外婆出现在画面中央的光亮处,四周的暗角阴影使画面充满了戏剧张力。对于导演蔡明亮而言,电影的本体是看不懂的神秘故事,是可供男女幽会的私密性场所,以及永远想得到的糖水凤梨——电影《是梦》的渴望。张艺谋选送《卢米埃尔与四十大导》的短片在长城上搭建了一个微型的电影拍摄现场,运用一个纵深镜头拍摄一对青年男女在长城上身着旗袍表演中国古典戏曲,又脱去旗袍表演摇滚演出的过程。在画面中可以清晰地了解电影工业机制的运作过程,而随着青年演员表演时长的增加,象征着胶片尺数的景深处的长城越来越长。对于导演张艺谋而言,电影成为先锋文明与传统历史的链接。
侯孝贤是以长镜头之中景深处的场面调度之娴熟著称的电影导演,韦斯·安德森则与其相对,从《月升王国》开始,韦斯·安德森就开始在自己拍摄的真人电影中不断依靠指挥机位或者说正面水平机位的移动创造扁平的二维画面,替代一般电影所强调或制造的二维中的三维纵深空间幻觉。在《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一度成为电影icon的影片中,韦斯·安德森以大量的过墙镜头以及极其艳丽的单一色调,将把摄影机的机械性极度放大的平移镜头与均匀的布光结合,为电影赋予了一种扁平感,告诉观众其在银幕上看到的真实的三维空间不过是一种二维画面上的绘画幻觉,以打破传统故事片中为完成叙事意志而对电影三维空间的封闭性要求。扁平的、开放的电影画面开始于一个独自走进风雪墓园的女孩,她在作家的墓碑前将手中的书转了一圈,镜头采用了标准的正反打拍摄墓碑上作家的照片与女孩的面孔,当女孩打开书,封面上的黑白照片变成彩色,作家直面摄影机开始了独白——这种打破“第四面墙”的拍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关于电影自身的媒介指认。在2011年这个胶片电影正式宣布死亡而数码电影时代正式到来的媒介转换的历史时刻,导演将自身对电影的思考再度引入媒介自身。
在火车车厢中,韦斯·安德森将主人公和身后的名画《苹果男孩》设计为正面水平机位的构图,画面下方放置的一个圆形反光凸面镜将同样身处在此刻空间中的穆斯塔法纳入画面中,从而告别了传统好莱坞中常用的对切镜头告知我们谁在观看、在看什么的叙事要求。同时,此刻的画面自然而然地也构成了一个运用镜像与画框帮助人物理解与阐释勾勒出重音符号的强有力的自指装置。
场域流动:空间延伸与互文叙事
本文首先需要对“互文”叙事进行一些概念上的厘清。“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范阈中的理论概念,诞生自法国文学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梳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过程中提出的“文本间性”,即“任何文本均构成于对于引言的拼接,一个文本即是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成为西方人文学科中的研究主流,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文化中存在一种普适的系统和结构关系,对于文本和实践的有关阐释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一对应。而“互文性”批评理论则是作为对待这种简单粗暴地将文本意义进行特征对应的结构主义的一种补充辩驳,在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开放性的同时,将固化的、静态的、单向度的文本影像变更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双向互动的生产场域。在电影的创作显征中,最常见的“互文性”是一种致敬经典的“引语实践”。如经典影片《低俗小说》(昆汀·塔伦蒂诺,1994)以喝咖啡的情侣劫匪致敬《邦尼与克莱德》(阿瑟·佩恩,1966),以朱尔斯行凶前的闲谈设计致敬《黄金大镖客》(赛尔乔·莱昂内,1966),以文森特为米娅胸口画圈注射致敬文学名著《百年孤独》,以布奇逃亡途中撞向马沙的剧情设计致敬《惊魂记》(希区柯克,1960),以布奇举起电锯杀害变态杂货店老板的镜头调度致敬《德州电锯杀人狂》(托比·霍铂,1974)。这些对经典电影经典镜头的引用重组一方面构成了《低俗小说》中黑色幽默的叙事基调,另一方面在对经典文本的引用中巧妙地建构了后现代主义电影的风格,完成了对当时好莱坞电影固有模式的创新。
作者电影中出现的电影装置以及银幕环境“链接了内外视域,链接了前后视域,链接了左右视域”,这种链接既是时空的联通,也是关系与意义的链接。这种链接为观众提供了崭新的观看视点——银幕中再媒介化的电影通过场域流通的形式实现了空间的延展。以亚利桑德罗·阿奎斯提的电影《触不到的恋人》为例,桑德拉·布洛克饰演的凯特·福斯特独自蜷缩在沙发上观看希区柯克导演的《美人计》。《美人计》这部被列为世界经典影片的电影本身已经是一部完整的成品,作为既得影像(Found Footage)被直接录制并不加任何后期处理的原始素材被摄入电影中。电视中的节目不断切换,凯特·福斯特孤身一人窝在沙发上,操作着手中的遥控器。而后镜头切换远景,画面左侧凯特·福斯特依旧保持着原有姿势,画面右侧的电视画面却停留在了正在播放的《美人计》上。电视中加里·格兰特饰演的迪普与英格丽·褒曼饰演的艾丽西亚·赫伯曼正深情拥吻,这一段情节是彼时电影史上最长的吻戏,而电视中浪漫的桥段却与凯特·福斯特当下的境遇迥然不同,她与恋人被迫分离在时空的两端,连见面都是奢望。此时的电影装置成为一种话语机器,出现在叙事的临界点上,凯特·福斯特孤独落寞的身影与《美人计》中亲密相拥的情侣分立画面两侧,显得格格不入。此外,迪普与艾丽西亚·赫伯曼拥吻的幸福画面也成了凯特·福斯特对爱情向往的互文叙事。这时,既得影像电影天然地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是附着在原始文本上的信息,二是原始文本与全新语境碰撞后形成的价值判断。”在电影作者有意识的选择之下,将既得影像从原有的语境之中剥离,使其原本的内容表达与自身叙事的表达相互呼应、相互衬托,进而完成超媒介装置对影片的互文叙事。
而侯孝贤在短片《电子公主电影院》中则运用大量远景的长镜头,宛如纪录片般客观地摄录下商业街对面影院外围的繁华景象: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影海报,来来往往的观影人群,花样繁多的零食摊贩(如图1)……而后镜头跟随着买票的母亲渐渐拉近,直到前来观影的一家人进入影院门口的红色幕布,画面在幕布的鲜红色中别入,叙事中出现了第二个时空:时间流逝之后的破败影院,镜头中的座位皮质破裂,露出令人尴尬的海绵碎屑,影院之内空无一人,天花板遮不住光,远处墙皮已经掉落,银幕渐渐出现主角童年时看过的黑白影像(如图2)。此时,导演侯孝贤对于现代已经没落的台湾电影院文化的哀愁就在这一组克制的镜头叙事之中完成了向观众的传递。观众和作为视点替身的电影角色置身于由装置延伸出的新的空间中,通过观看与被观看的错位关系推倒了观众与电影之间的“第四面墙”,构造出电影叙事中的崭新美学。“图像被从原先嵌入时空和叙事的连续性中摘取出来,他们在那里获得了其最初要表达的意义。”

图1 《电子公主电影院》繁华景象(图片来源:《电子公主电影院》台湾导演侯孝贤作品)

图2 《电子公主电影院》破败影院(图片来源:《电子公主电影院》台湾导演侯孝贤作品)
就电影行业尤其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主流商业电影的行业现状而言,电影生产的过程是一条规模庞大的工厂流水线,众所周知,工厂中需要的只是无意识的螺丝钉与齿轮,而非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因此,将传统人文主义重新引入电影的“电影作者论”便成为对已成沉疴的电影工业系统的某种颠覆与反抗。
作为在稳定的封闭时空中通过视听语言建构出来的叙事连续体,电影艺术利用时间、空间、视觉、听觉这四个因素的叙事编码为观影大众打开了一扇可以窥视世界的窗户。而再媒介化的电影装置的出现,无疑能为观众建构一个崭新的、超越的世界,或是某种独创的观看视角,在大众媒介形态之中再生新的景观,“以富有原创性的视听语言表达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用某种疏离沉静地临渊回眸的姿态展示表层现代主义文化之下的荒芜”,即通过对媒介自身不可逾越的挑战,丰富当代影视创作中人文与反人文的哲学玄思,将创作者代入更为广阔的、富有艺术价值的作者电影的创作之中。
参考文献
[1]李啸洋.界与域:装置艺术在电影中的再媒介化[J].当代电影,2018(08):118-120.
[2]贺万里.中国当代装置艺术史(1979—2005)[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3]苏状,马凌.屏幕媒体视觉传播变革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4(08):123-129+144.
[4]明朝.电影作为现成品——既得影像电影的基本模式与美学特征[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02):44-57.
[5]戴锦华.电影批评(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董冰峰.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7]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M].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8]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上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