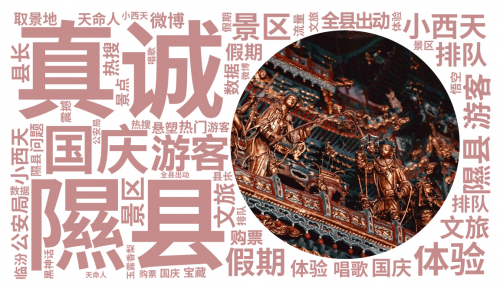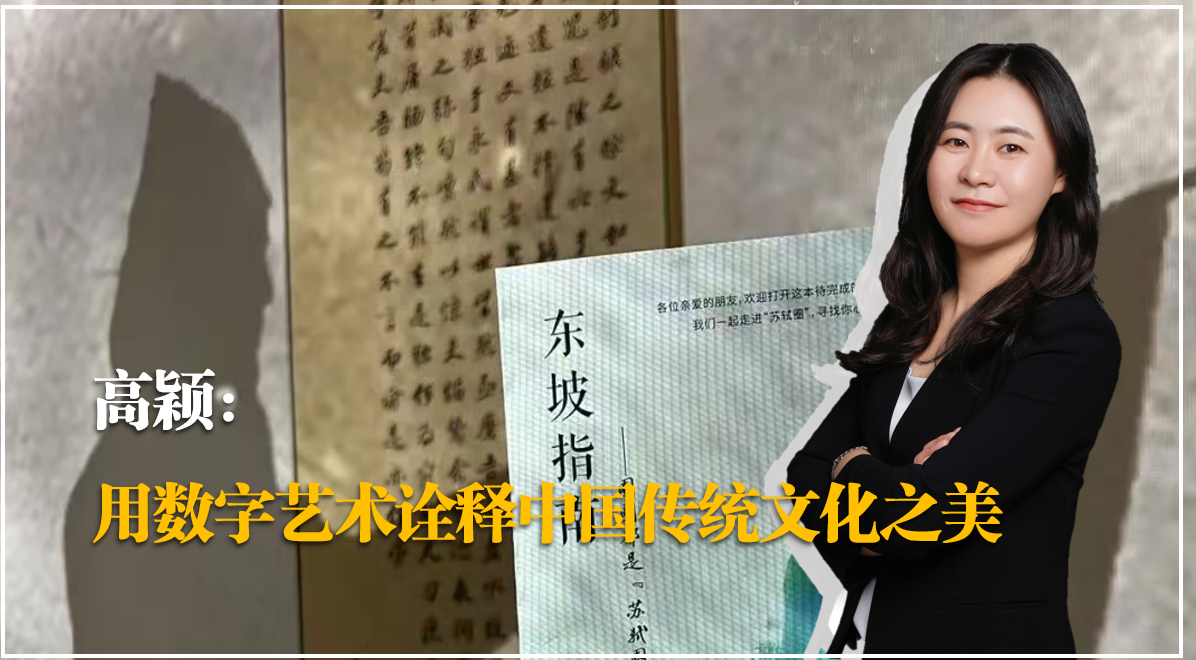集体记忆的建构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提升民族文化凝聚力促进文化的发展。以关中社火为载体,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了解民间社火传播的方式,即以身体在场的传播为主。新媒体影像技术使得民间习俗更加生动鲜活,但制作内容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传统习俗。在风险社会中,传播集体记忆和构建集体认同的方式受到了冲击,亟须探寻强化集体记忆的新路径。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集体记忆最早由法国学者哈布瓦赫提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1]。在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哈布瓦赫强调建构主义,而在功能主义研究视角中,保罗·康纳顿认为,群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作用。钟年强调集体记忆的重要性,认为离开社会记忆,将无法把握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2]。近年来,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越来越多,涉猎学科也越来越广,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种电视剧、电影、短视频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也越来越多。有研究者认为,短视频以丰富的传播形式、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传播主体、跨平台的传播范围等特点成为传播传统文化和建构传统文化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3]。新媒体空间也建构了不同的集体记忆,并维系了社会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人的完整性,但对民间社会的集体记忆关注较少。民间社会作为我国最古老的社会形态,其集体记忆也是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集体记忆是怎样建构的,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为了考察民间社会的集体记忆,笔者选择了一种具体的民俗形式——社火。这种形式把抽象的、宏观的集体记忆研究聚焦于具体的形式。交流的前提是传受双方有共通的意义空间,而方言在民间习俗的考察中具有优势,也更容易获得受访者的信任。基于笔者所处的地理空间位置,选择渭南市D村作为田野调查对象,在2022年7月中旬至8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选择D村是因为该村人口数量较多,有社火活动,在周边村镇中小有名气,也是关中社火的传习基地之一。
访谈法是通过和受访对象面对面交流来了解研究对象,从而揭示研究对象的潜在动机、信念、态度和感情的一种方法。笔者有目的地抽取了6人作为访谈对象,研究D村社火的传播方式以及习俗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中有3名老年人(年龄都在60周岁以上且参加过5届以上社火活动),2名中年人(年龄在35周岁以上且参加过2届以上社火活动)和1名青少年(随机抽取一位大学生,观看过1届社火)。
关中社火的缘起与发展
社火,又称“射虎”(陕西话读音),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庆典狂欢活动。社火的表演内容包括跑竹马、踩高跷、高台、舞狮、舞龙、扭秧歌等,具体形式往往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举办社火表演之际是一年中村里最热闹的时候。“社”是指在祭祀或节日期间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表演。民间以户族设“堂”,以村、堡设“社”,与“社”有关的事称“社事”。“火”具有红火、热闹之意。D村的社火起源于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即“尧山爷”。“尧山爷”又称尧山圣母,是伴随着请神送神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仪式,组织性强。圣母是尧帝的女儿,和西山的“爷爷”是姊妹俩,但两人吵架了,圣母不吃韭菜,而西山撒了韭菜籽,“尧山爷”便来到了尧山。D村毗邻尧山的村镇,为求风调雨顺,村民们每年都会轮流迎接“尧山爷”,因此有了社火表演,也称“打社火”。这里的“社”是从原来的农业社(农村集体合作社)中衍生出来的。尧山圣母到哪个社,哪个社就庄稼兴旺,因此村民每年都会争抢着去请圣母。1个村为1社,一共有12个社,D村是第九社。每逢D村打社火,村民都非常积极,甚至有的村民会因为社火而暂时推掉工作。
研究发现
(一)社火的传播方式:身体在场
社火的传播方式以家庭内的人际传播为主,每年的社火展演大多以大众传播为主,这是一种身体在场的传播方式。在场包括两层含义,所谓“在”,是指主体的“在”,没有主体就谈不上是否在场了;所谓“场”,是指特定的空间,正是这个空间构成了主体所在的环境以及发生在主体身上的事件,这个环境或事件中也包括其他人[4]。访谈对象D表示,家庭内的传播是晚辈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以及在每年的社火仪式中耳濡目染完成的,因此,社火已经融入每个人的认知框架中。每年的社火表演预备周期长,宣传力度大,周边城镇的人纷至沓来,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下,基于身体在场的体验,受众会形成对社火的认知,从而促进社火习俗的传承与传播。
在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为社火习俗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村民可以线上观看社火。访谈对象E表示:“现在科技发达了,能通过朋友圈、短视频来观看村里的社火,但那种感觉和自己去现场参与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家那肯定是要参加的,比较热闹嘛,大家聚集在一起都很高兴。”也就是说身体在场仍然是主要的传播方式。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一旦身体缺席,参与者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克服它,比如我们会追求模拟身体在场的交流方式,不再满足于使用文字进行交流,要能看到图像,听到声音[5]。
(二)民俗传播与身份认同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认同’就是‘我是谁’的问题,而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于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神像的生产制作是村落身份的象征和村落认同的标识,各大庙宇的神像是区域的守护神,具有团结村民的功能,塑像也表征地域身份,具有建构地域身份认同的功能[6]。尧山圣母的雕像建构了D村的地域身份认同。受访者E表示:“大家家里基本都有圣母神像。”圣母神像从寺庙拓展到公共生活空间,成为一种符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反复传播,使神像意义变得更加丰富。尧山圣母呼风唤雨、造福人类的形象在传播中得以巩固和内化,并产生了文化认同。
(三)不断变动的集体记忆
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形成了D村村民关于社火的独特记忆。在问及社火时,访谈对象不约而同地表示,“当然知道了”“那是我们村的传统,我都看过打社火呢”。哈布瓦赫曾说:“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7]一个社会中有多少个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不同的记忆。随着社会的变迁,每代人形成了不同的记忆。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非常了解社火的历史渊源,而年轻一代,如35周岁以下的青壮年更多地认为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他们的记忆更多的是关于社火表演时欢腾的气氛或场面。对于讲述过去,老年人要比年轻人更积极。他们不会试图等待记忆复苏,他们会试图使记忆更加准确,通过询问别的老人,或者查看信件、文章等讲述自己记忆中的内容[8]。遗憾的是,记忆往往伴随着遗忘。人们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可能会遗忘一些消极的、不愉快的内容。在每年的接圣母环节,社与社之间也发生过冲突。因为圣母是神圣的,按照顺序未轮到的村社,也可能会派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去抢。但访谈对象很少谈到冲突事件。
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每时每刻都在重构过去,但往往也在歪曲过去。为了调整记忆,使其适应社会的变化,社会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消除导致个体彼此分离和相互疏远的记忆[9]。如果经过较长时间再回访这些受访者,他们关于同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是保持前后一致性的必然结果。
(四)新媒体重塑新的记忆
建构习俗文化的集体记忆需要社会互动,社会个体唯有在社会情境交流中才能获得记忆,并对这一情境进行识别和定位。而互动性正是新媒体的特征,其可以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打破二者之间的空间界限,使受众真正了解习俗文化。在新媒体传播背景下,很多新元素可以被附加到社火表演中,如各种表情包、贴纸、音乐等,它使得习俗传播不再是刻板的、呆滞的,更能吸引受众。在新媒体文化熏陶下的社火记忆与世代口耳相传的社火记忆碰撞出新的火花。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居于中心地位[10]。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不同媒介构建不同的记忆,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更加真实,文字媒介的传播更加长远和持久,视频图片等更加鲜活生动,但也要警惕新媒体传播带来的消极影响。访谈对象C说道:“有些关于社火的搞笑视频,看得人既好笑又好气,我们都是有尺度的‘热闹’,到网上就被无限放大了。”倘若一味地追求视频的浏览量、转发量等量化指标,社火传播就会以戏谑为取向,丧失了文化韵味。借助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文化。
由于存在数字鸿沟,D村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率低、识字率低,他们很难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或一些民俗文章来巩固或重构社会记忆。新媒体赋予年轻群体鲜活的社火记忆,而老一辈人仍然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播断层等现象的出现。
(五)风险社会对集体记忆的冲击
传播一词包含两层含义,分别为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传播的传递观主要与讯息的编码和传送有关,聚焦于与效率、效果有关的问题[11]。而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仪式观更强调传播对社会共同体的维系,D村的社火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在排练社火的过程中,村民个人身份的差异性被弱化,他们成为具有同一身份标识的群体,如“秧歌方队”“锣鼓队”等,这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伴随每年的社火展演,人们会不断更新和强化自己的记忆。风险社会充斥着很多不确定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追求功名利禄,精神信仰越来越贫乏,村里的聚集性仪式减少,村民之间的交流沟通也随之减少,以前积累的习俗记忆逐渐淡化。
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形式都有偏向,以传播的本性,它最擅长缩短发送信息的时间并控制空间,或强化集体的记忆与意识并控制时间。”[12]社火强化了社群记忆,并使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现代化进程对时间的吞噬使得“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更加明显。访谈对象B说:“我们这一辈人年纪大了,下次打社火可能身体就不行了,村里那些年轻小伙,他们是主力军。”“我们”是年长者,参加过很多届社火展演,经验丰富,对各种流程了如指掌;“他们”是年轻一代,需要在“我们”的指导下完成社火展演。
D村社火的传播方式以家庭内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主,新媒体带来的新的传播方式并没有对社火的传播方式造成冲击,身体传播仍是主要的传播方式。D村的村民不断重构着关于社火的集体记忆,由于记忆具有遗忘性,且容易出错或歪曲,因此他们会遗忘不愉快的群体记忆。新媒体带来的广阔的传播舞台使得社火表演中表演者的形象更加鲜活,但由于传播者的自主性太强,对传统习俗有所破坏。在民间习俗造成了一定冲击时,我们应该探寻强化集体记忆的新路径,维护时间带给人们的财富。
艾宾浩斯通过研究,发现了遗忘与重复之间的规律,即“人的记忆和遗忘之间存在周期,按照固定的时间对记忆加以重复,就会使记忆变得更加清晰”。民俗文化要考虑群众的意见,如此才能增强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信。首先,可以建立专门的微信公众号来向受众传输信息,同时推出社火小游戏、社火知识大课堂等App,便于受众在手机上了解社火活动,加深受众对社火的认知和理解。其次,每逢过节,可以组织小规模的社火展演,划分若干小组,让其分别承担不同的演出任务,以小范围、多频次的演出形式强化人们的记忆。最后,依靠数字化媒介对社火习俗进行传播,对社火习俗的影像资料进行保存,对圣母庙内的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从而形成系统的资源数据库,促进社火习俗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7][8][9]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钟年.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族群意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4):25-27.
[3]洪雨.短视频对传统文化集体记忆建构研究[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21.
[4]赵建国.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08):58-62.
[5]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40(02):37-46.
[6]帅志强.民俗传播:妈祖雕塑的视觉修辞与身份认同[J].未来传播,2022,29(05):66-74.
[10]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09):39-50+126-127.
[11]戴维·J·贡克尔,保罗·A·泰勒.海德格尔论媒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
[1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