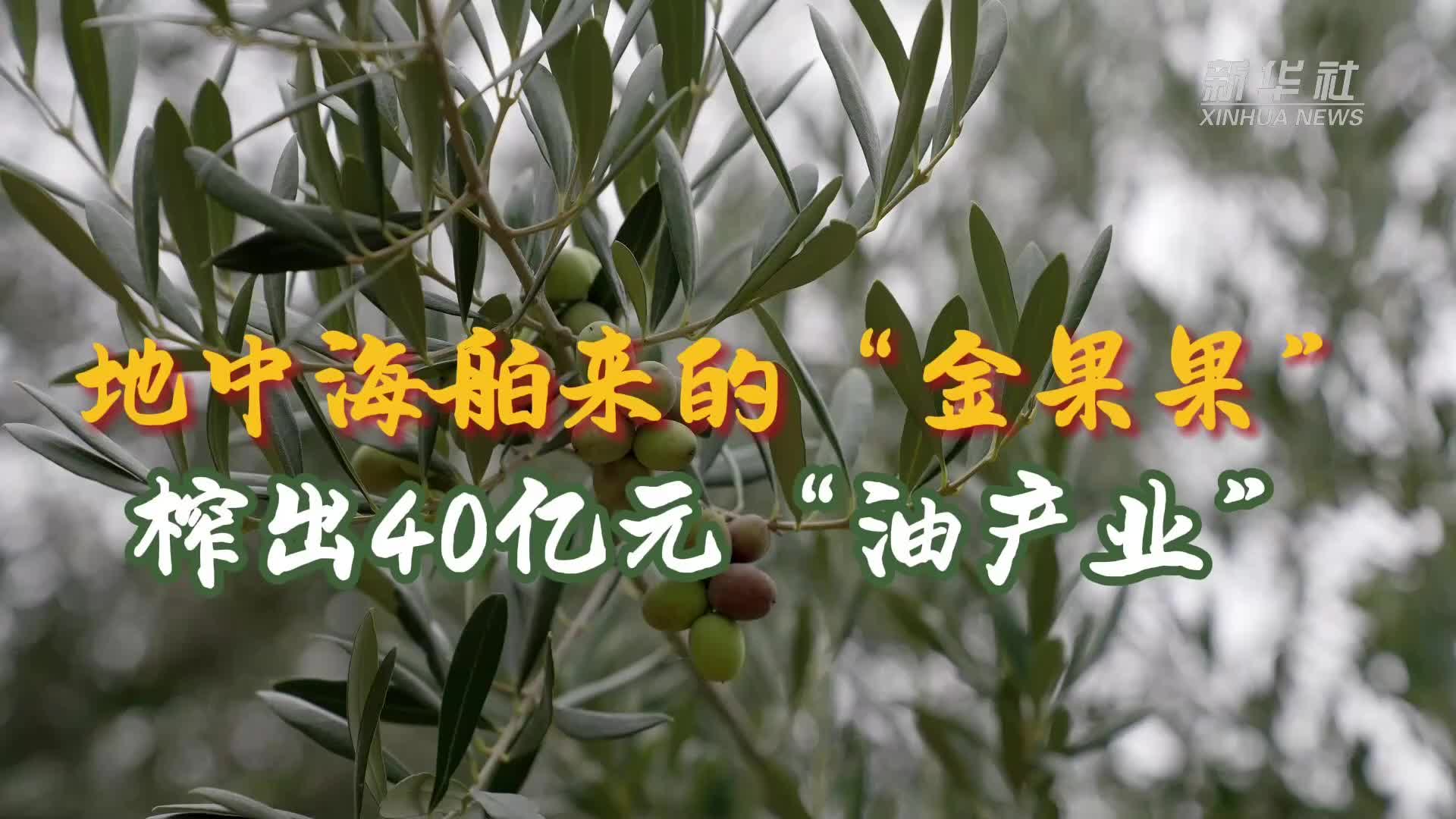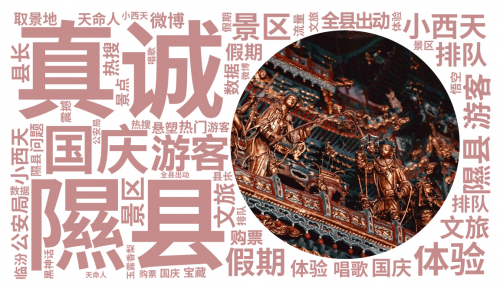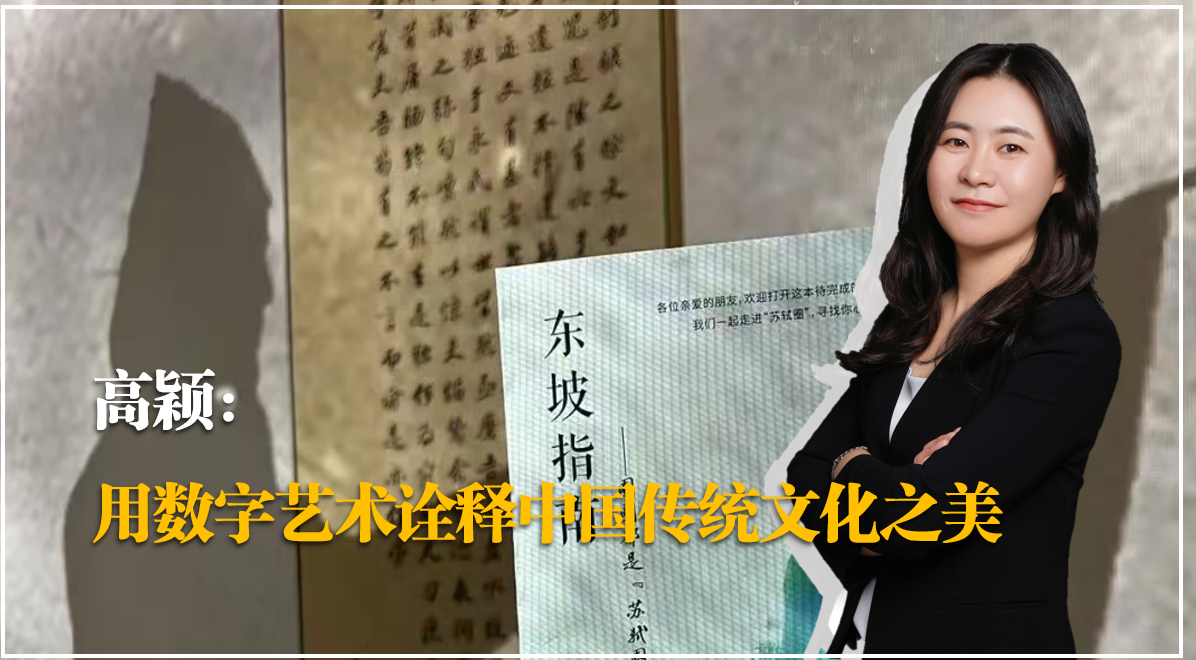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电影中涌现出“新文人电影”“小文人电影”等创作主张和现象,大量院线电影借助水墨元素、中国画式的构图进行了影像文人化尝试。这些电影创作形成了文人化风格趋势,对“文人电影”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重塑。现通过比较研究《小城之春》和《春江水暖》两部影片中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呈现,探讨两部影片与中国古典思想及艺术间的关系。《小城之春》化用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愈加精练而抽象,其象为形之精华,对应《周易•系辞》中的“在天成象”;《春江水暖》则在挪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愈加繁复而具体,其形为象之体质,对应《周易•系辞》中的“在地成形”。
“泛文人电影”文本溯源与概念演化
“文人电影”这一术语由香港学者黄继持提出,他将20世纪30年代电影工作者与新文学作家合作拍摄的电影称为“文人电影”的开端。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知识阶层的社会身份定位随之改变,文人身份的基础——士人阶层——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因此当下的文人化电影创作很难在真正意义上被视为“文人电影”。而经典“文人电影”虽是相互关系松散的电影文本系列,却被认为具备视觉与叙事特征,其题材、影像、风格、情绪、技术手法可以在任何层面被改编和继承。因而,“文人电影”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延展性和神话力量,其作为一种电影实践模式,在后世呈现出一种泛类型片的面貌——“泛文人电影”。
拍摄于1948年的《小城之春》是“文人电影”中的典范,而20世纪50年代的《林家铺子》、60年代的《早春二月》及80年代的《城南旧事》也都被视为“文人电影”创作脉络的延伸。这些影片不仅在形式、内容和美学层面呈互文关系并体现着文人意趣,更将中国古典人文精神融入电影艺术语汇,共同组成了“泛文人电影”创作传统。
在近几年涌现出的电影作品中,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小城之春》极为相近。一方面,两部影片都与中国传统绘画和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小城之春》取象于苏轼的《蝶恋花·春景》,《春江水暖》的片名取自苏轼为画作《春江晚景》所题诗作。另一方面,两部影片片名中都有一个“春”字,《小城之春》的片名既有时间的表述,也有空间的表述,其“春”字着眼于时间;而《春江水暖》中的“春江”指富春江,春字着眼于空间。对时间与空间的呈现是两部影片形式上的核心问题,费穆提出“空气说”,他认为《小城之春》在独白和倒叙的时间中展现了具有多重隐喻意味的空间;顾晓刚则提出“人物共享时空”概念,他认为整部电影最大的主旨或者说美学方面的努力就是达到山水绘画的主题——时间与空间的无限[1]。
造境与写境:差异化的空间呈现
两位导演的影片均从中国画中汲取养分,而在如何实现电影与绘画媒介间转换的问题上,二人的理念却迥然有别。理念的差别进一步使得长镜头的使用在影片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也使影片的空间表现呈现出“造境”与“写境”的差异。
(一)媒介转化问题的认知差异
费穆认为“中国画是意中之画”,“用主观融洽于客体……却不斤斤于逼真。那便是中国画”。其强调“意中之画”而非写实,体现了“主观融洽于客体”的物我齐一思想。电影学者李少白曾指出,“对城墙‘抽象的表现’仿佛京剧中的城墙景片,可以理解为费穆在电影中‘作中国画’的尝试”[2]。即城墙是故事发生的场景,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还是景片式的抽象存在[3]。在此意义上,城墙是“主观融洽于客体”的“意中之城墙”,而非客观实在。
顾晓刚则强调山水在影片中的核心地位。他曾表示,“中国传统卷轴绘画展开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可能刚开始没有人和景物,只有房子。或者说没有剧情,只有景色……从那个时候就把它理解成一幅画了,不是电影”。顾晓刚怀着绘画的心态去拍摄山水,“空镜头”即成为“空景”,并将人物、剧情放置在山水中,从而构建了电影的“绘画感”[4]。影片不仅通过富阳方言突出其地域性,还用导游般的语气借绘画、诗歌、歌曲来强调这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富阳。
费穆重写意,空间具画意而片中无画,《小城之春》中的空间并非客观实在;顾晓刚重写生,着力将电影拍成风景画,片中也出现了画作的特写镜头,《春江水暖》的空间为客观实在。因而尽管两部都使用长镜头,但其作用和意义却迥然有别。
(二)长镜头作用:表演连贯性与“绘画感”
长镜头不仅是表现所谓“东方美学”的便捷手段,也是保证欠缺表演能力的演员能够进行连贯表演的重要方法。关于《小城之春》的长镜头,演员韦伟谈到,“假如他不是连贯地拍下来,我们就不可能演得好,因为我们把握不住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尺寸。”费穆强调电影之织接完全是属于技术的,每一画面之间,演员的情绪因时间的关系而不免有相当隔离,因而难以勾起演员的真实情感[5]。他通过长镜头以保证表演连贯自然,而长镜头与“美学”和“绘画感”并无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长镜头并非必要形式[6]。
《春江水暖》中的长镜头则是表现“绘画感”的主要形式,已有多位学者从“手卷式电影”“卷轴美学”及“诗意视觉”等角度对这种创作倾向进行过论述。以导演顾晓刚自己的话来说,“《春江水暖》的长镜头原理其实已经不来自电影之中,而是中国传统绘画”。即《春江水暖》中的长镜头是衔接绘画与电影艺术语汇的手段,也是实现“绘画感”的必要形式载体[7]。
(三)“造境”小城与“写境”富阳
两部影片均表现江南小城,也都拍摄于江南小城。《小城之春》的外景地位于上海松江,城墙、旧屋虽是影片血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影片中却并未明确交代“小城”的具体位置。《春江水暖》拍摄于浙江富阳,与前者相反,导演在片中多次强调了故事的发生地。
《小城之春》虚写小城是必然的,因为小城是隐喻空间。影片仅集中于荒城与废园展开情节,或许对费穆来说,仅把握这两个空间意象已经足够。而影片中戴礼言的台词“我的身体,怕跟这房子一样,坏得不能够收拾了”暗示戴礼言与废园是一体的,而废园又指涉破败的旧中国,即人、空间、家国是一体的。参照《人间词话》的框架,就拍摄材料而言,《小城之春》的空间呈现属于“造境”。
《春江水暖》则对富阳进行了全景式的写实展现,如顾晓刚所说:“整部电影都在讲空间。”影片对多样空间进行了景观式的抒情展现,山水、饭店、医院、公墓、旧小区、新楼盘等[8]。导演以纪录片的方式展现种种空间,让《春江水暖》的创作更偏“写境”。
《小城之春》重写意,践行“空气说”,主要表现荒城与旧园两个空间,于“无我之境”中“造境”小城,创造独有的心理空间以关照家国、文明的前途命运。《春江水暖》主写生,尝试“空景”观,以全景展现城市的多样空间,以“有我之境”的口吻“写境”富阳,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记录真实空间以突出地域文化特性。
“永恒轮回”时间观念
两部影片都是作者有感于时代的变动,以影片表现其时代,片中均呈现出了“永恒轮回”的时间观念,但在叙述形式和时间观念上,两部影片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
(一)时代感怀与叙事形式
《小城之春》孕育于1948年,彼时的中国大地正处于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时期。影片筹备了不足一个月便开拍,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解放战争打响后暂处于和平时期的小城,而费穆正是怀着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心境拍摄影片,体现了锦绣江山“流产”后费穆内心的真实写照。
《春江水暖》拍摄历时两年,上映于2019年。导演感怀于富阳在“G20峰会”之后撤市变区,并为了承接2022年亚运会的部分项目,整个城市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更新,拍摄了这部影片。《春江水暖》对富阳旧楼拆迁、房价上涨、地铁修建等进行了客观展现,纪录片式地表现了城市发展进程,体现了导演的现实关怀。
在叙事形式方面,《春江水暖》为多线顺叙,片中经历了从春至冬一年的时间。导演所处的时间与影片中的时间同步,是对当下的客观纪录且具有确定性;《小城之春》是戏剧性叙事,讲述了十几天中发生的故事,而费穆现实中所处的时间要晚于《小城之春》中展现的时间,是对处于历史关键节点前夜的小城和平生活的或然性创造。
(二)确定性与或然性的时间观
《小城之春》以玉纹的独白展开叙事,其梦呓式的视角和时态不停变换,时而主观时而客观,或现在进行时或过去进行时,呈现出一种“像是喝醉,像是做梦”的叙事混沌状态。同时,影片多次结合独白与影像营造同义反复,如镜头已清楚表现玉纹换完衣服在梳头,偏加上独白“换了件衣服,整理了一下头发”。费穆于众所忽处不忽,看似啰唆的同义反复,却产生了别样的美感与意味。然而在戴礼言自杀后,玉纹的独白便不再出现,视角也转换为第三人称客观视角,可见导演的洒脱烂漫不为形式所囿。影片还运用剪辑技巧,制造出时间的跳跃感和断裂感,于暧昧的画外时间中营造“悬想”感。综上,费穆在《小城之春》中营造的时间观是或然的。
《春江水暖》的时间观营造则要现实得多。顾晓刚曾表示,“中国山水画的叙事,就在于‘人物共享时空’,在一个统一时空中产生了并行叙事,层峦叠嶂,我们电影中做了大量这样的处理”。“人物共享时空”似指多人物多视角顺序叙事,而“统一时空”则体现了《春江水暖》的物理学时间观[9]。这种纪录片式的客观时间多视角展现了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结尾回到夏天寿宴前的夜晚,回到导演的主观时间,是导演的主观与客观时间的交织,其时间观是确定的。
(三)“永恒轮回”的差异化呈现
两部影片都创造了时间的循环,形成了一种“永恒轮回”的时间感。《小城之春》中时间的循环极为特殊,开篇即表现结尾。“《小城之春》开始使用了倒叙手法——在片头之后,戴秀和志忱手挽手在佣人老黄的跟随下走向远方。”显然这是费穆导演借助“倒叙法”营造“悬想”的又一次实践[10][11];而章志忱离开的结局仿佛已经发生或者注定发生,全片所讲述的故事宿命式地必然发生。影片呈现了无尽时间之流中小城的时间切片,并定格于该决定性瞬间,从而形成时间的循环。虽然片中人物仅表现出一种苦闷的状态而无激烈的戏剧性动作,但此苦闷状态的情感和戏剧性强度极高,看似平静的生活实则暗流涌动,人物处于生命能量极高的“烦”的情境。影片并未解决问题,而是将情感真相公之于众,以期取得谅解与宽容,从而消解部分问题,并悬搁无法解决的问题。
《春江水暖》中,能直观看到的春夏秋冬,再加上结尾的一个回闪,再次回到了夏天寿宴前的那一夜,形成了一个时间的轮回。借自然呈现一些人生观念、轮回观,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人式的表达。顾晓刚试图通过结尾的闪回,以达到“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和“宇宙感”[12]。如同片中多次出现的老照片,《春江水暖》侧重对往昔的回顾和眷恋。
虽然两部影片都形成了“永恒轮回”的时间,但《春江水暖》呈现的是确定性的时间观,结尾创造时间循环以追忆过去;而《小城之春》为或然性的时间观,结尾打破时间循环以面向未来。《小城之春》结尾处过去与未来、电影时间与现实时间的碰撞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意义。
结语
两部影片是传统“文人电影”和当下“泛文人电影”的重要文本,都立足于中国传统,对既有艺术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了转译并融入了电影艺术语汇。但创作思维与理念的差异,以及创作者与中国古典思想及艺术间的距离是两部影片形似而神不似的原因。
《小城之春》开拓古典精神,顺现代主义潮流,化用中国古典思想,愈加精练抽象,对应《周易•系辞》中的“在天成象”。《春江水暖》怀抱传统情结,承现实主义传统,挪用中国文化元素,愈加繁复具体,对应《周易•系辞》中的“在地成形”。
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文人电影”的概念超出了中国电影理论的学术范畴,也超出了中国电影创作历程的历史范畴,它协同塑造了中国民族电影文化的自我建构与创作实践。因此,探讨“文人电影”及“泛文人电影”创作传统的问题已超出内容题材、影视技术和视觉元素的范畴,对此,应秉持“以中释中”的路径,在中国古典思想与艺术的框架中梳理电影文本的人文价值内涵,以期回归“文人电影”的创作理念与内在逻辑,回归“文人电影”与中国古典思想及艺术的联系,进而开辟出新的“泛文人电影”研究与创作领域。
参考文献
[1][7][9][12]顾晓刚,苏七七.《春江水暖》:浸润传统美学的“时代人像风物志”——顾晓刚访谈[J].电影艺术,2020(05):98-103.
[2][5][6][11]黄爱玲.诗人导演费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3]李少白.中国现代电影的前驱(下)──论费穆和《小城之春》的历史意义[J].电影艺术,1996(06):73-78.
[4][12]导筒directube.导筒×导演顾晓刚:从泥泞的沼泽中走出,用影像打开漫漫长卷[Z/OL].(2019-8-19)[2022-12-01].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422810/.
[8]FIRST影展.《春江水暖》|中国长卷绘画与视听语言的完美结合[Z/OL].(2019-07-26)[2022-12-01].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339969/.
[10]苏文瑜,朱怡淼.费穆电影《小城之春》中的美学与道德政治[J].当代电影,2016(08):8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