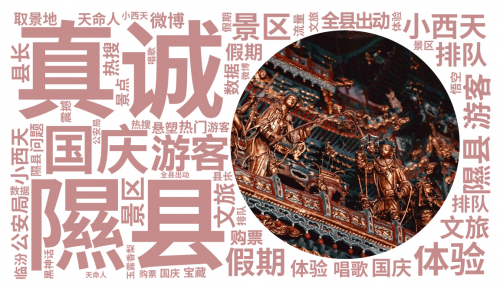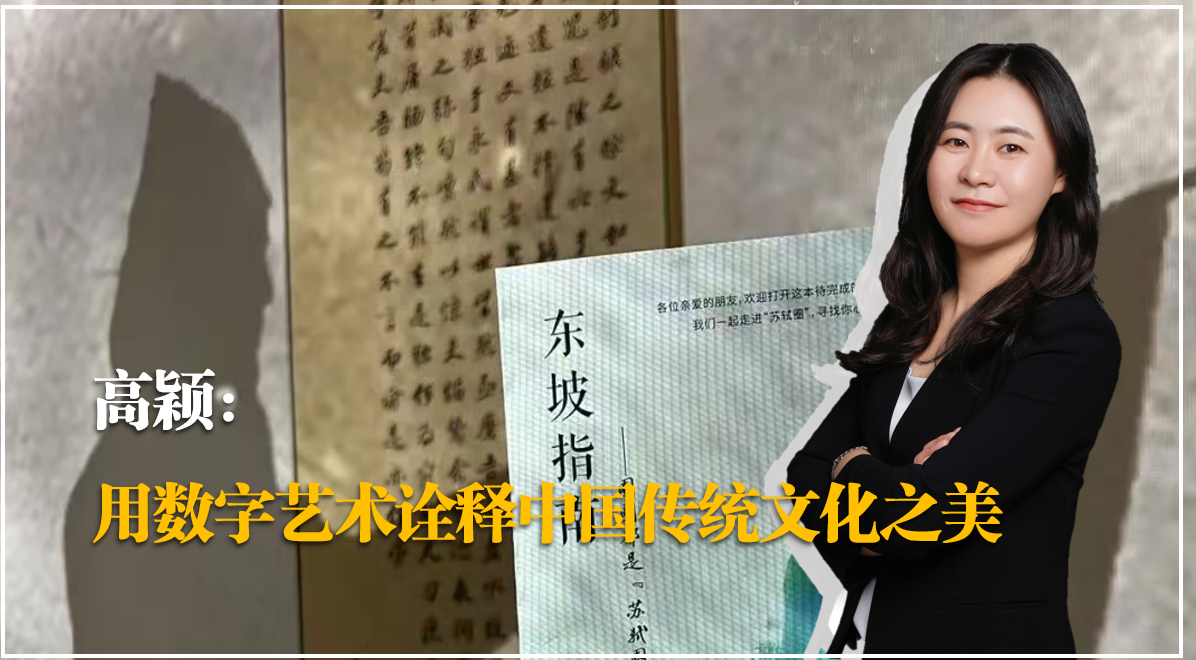先秦出土文献阅读推广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经典阅读新风尚,唤醒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出土文献阅读推广体系等特殊意义。出版机构及出版行业从业者应加快普及性读物出版以打破“绝学”壁垒,提升教材相关内容占比以打牢语文教育根基,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推动先秦出土文献融合出版,培养专业的出版和发行人才队伍,为先秦出土文献的出版发行抢占先机。
阅读推广的内容(文献)有其传统、固定的一面,但也并非一成不变。新文献的发现、生产、出版会对原有内容起到补充、更新的作用,拓展阅读推广的领域和视野。以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为例,传世文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上千年来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整理研究和注释解读文本模式,它们是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主体。近年来,大量先秦出土典籍文献面世,但在阅读推广领域尚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需投入更多的关注。
之所以要格外重视先秦出土文献的阅读推广,一方面是由于当前新材料的典藏出版日臻丰富,其保存、整理与研究状况已非昔比。随着出版水平和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先秦出土文献也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天书”。另一方面,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语境下,阅读推广需要在既有材料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领域,形成新的热点,先秦出土文献阅读推广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先秦出土文献阅读推广的重要意义
(一)梳理普及汉字源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先秦出土文献最显著的特征是书写形态的原始性,其保留了汉字书写的早期信息,如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有序,汉字的相对稳定是贯穿始终的管钥。要想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需要在全社会普及汉字知识,让公众了解、掌握汉字发展源流。否则,对文本的解读、对文化的阐释都会变成无根浮萍,无法把握其根脉所在。
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人民政府八部门联合发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正式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2021年2月25日,“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成立,其主要职责是为古文字工程实施提供学术咨询和专业指导,统筹提出工程实施计划,论证项目研究规划,审议工程预算方案,并对工程进展和成效进行评估等。这些举措足以说明先秦出土文献因其独特的文化源头性价值,正受到顶层规划和社会各界的日益重视。
(二)重建传统文本阅读体系,引领经典阅读新风尚
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传世文献,经过上千年辗转抄印,已出现了许多文本上的偏离甚至讹误,只是在阅读推广和语文教育中,很少特意去指出这些问题。先秦出土文献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传世文献的校订,帮助重建传统文本的阅读体系,即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1]。
数字化时代,阅读碎片化、娱乐化倾向严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数字时代固然需要建立阅读新形态,普及阅读新风尚,但也不能过度挤压甚至废弃经典阅读的空间。先秦出土文献阅读推广是经典阅读推广的重要抓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当下阅读碎片化、娱乐化的倾向,引领经典阅读风尚。通过阅读先秦出土文献,可以培养读者勤于搜集材料、善于多元思考的良好阅读习惯,这与阅读推广的根本目标相契合。
(三)唤醒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提升古籍文物保护水平
传统出版物以纸张为载体,随着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的推广,虚拟阅读呈现席卷之势,读者在阅读文字之余可以体会到数字载体带来的阅读质感和文化互动。而先秦出土文献除了前文提到的书写形态原始性特点,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书写载体的多样性,包括龟甲、兽骨、鼎彝、简牍、丝帛、玉石等。
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教育培训和理念灌输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但大多历史文物都躺在博物馆的库房或橱窗里,公众难有直接接触的机会。而通过阅读先秦出土文献,读者有机会对其载体产生直观了解,认识到历史文物的重要价值,这有利于初步培养读者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进而丰富读者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感性认识,最终达到唤醒读者深层次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目的。
(四)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出土文献阅读推广体系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是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嘱托,也是对传承推广传统文化事业的嘱托。
尽管一些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度都有出土文献存在,但像我国这样体量巨大且文字文本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绝无仅有。从先秦到晚清,学者文人总结出了许多与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相适应的阅读方法,如《朱子读书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值得传承发扬。对先秦出土文献阅读推广模式的探索,有利于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出土文献阅读推广体系。以“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协作发展为平台,将我国的出土文献和传统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让中国故事的内涵更丰富,让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深远。
阅读推广视域下先秦出土文献出版发行的问题与对策
先秦出土文献尽管被冠以“文献”之名,并具有无可比拟的经典性、传承性和学术性,但在阅读推广的视域下,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充其量是在传统文化或经典阅读推广过程中被附带提及。总体来说,相较于人们对传统古籍与传世文本的推崇,先秦出土文献似乎还处于极为边缘的位置。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天书”般的文字造成显著的阅读障碍;“经世致用”的功利思想阻碍经典文献阅读推广;缺乏专业阅读推广人才队伍,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出版业有责任也有能力挺身而出,为先秦出土文献的阅读推广贡献力量。出版机构和出版行业从业者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先秦出土文献的出版事业发展。
(一)加快普及性读物出版,打破“绝学”壁垒
长期以来,以古文字学为中心的先秦出土文献学被视为“绝学”,因其难读难认,更难于研究利用,专业学者尚须皓首穷经,普通读者更是难以接近,其阅读推广的难度也在于此。在甲骨金文、简牍帛书与现代汉字书写的文本之间,读者无法建立良好的认知联系,更无从谈由此获取知识与培养阅读的能力。
其实,阅读先秦出土文献的门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尽管中国古代的金石学、小学已有上千年的学术传统,但古文字学的真正发展是在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后,近几十年才逐步走上科学化、系统化道路,因此并非无法逾越的鸿沟。按照著名古文字学家林沄先生的看法:“真正作为搞古文字研究的先决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有阅读繁体字的古代典籍的基本能力。至于其他知识,有了自然更好,没有也不要紧,在研究古文字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需要随时去学。”[2]所以,所谓阅读先秦出土文献“绝学”的壁垒,是完全可以打破的。
另一个是释读意见的统一问题。自1899年甲骨文被认定发现以来,科学的古文字学研究尚只百余年。面对海量的旧材料和不断发现的新文本,学者的释读往往歧见迭出。同一个字有数种甚至数十种不同的释读意见,在古文字学界比较常见,令人不知所措。文字释读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本的推广普及。相对来说,传世文献较稳定的文本系统更便于读者接受。毕竟,连专业人士都还聚讼纷纭,又如何进入大众视野。
综上所述,出版高质量的普及性读物,是先秦出土文献阅读推广的重要一环。学术界应努力加快学术转化,将深奥晦涩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知识通过非学术化的表达普及给普通大众。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投入这项工作中,着手编写一些普及性的读本或文字编。如凤凰出版社于2017年推出“古文字读本”丛书,选取先秦文字中具有代表性的各类形态,通过图版、释文、注释、延展阅读等部分加以介绍,颇适合初学者使用[3];刘钊、冯克坚主编《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以《新甲骨文编(增订本)》为主要依据,收录甲骨文中已释的常用字,既可作为专业研究者便于翻检的工具书,又可作为初学者熟悉甲骨文的入门阶梯[4]。
不过,目前先秦出土文献读物的编纂出版依然以“文字”为中心,而非“文献”。在今后相关书籍的出版过程中,应注重“古书”“古史”“古文字”三个维度的结合,让读者由“文字”进入“文本”,由“文本”进入“古书”,最终完成阅读推广的核心任务——文化滋养。
(二)加强相关教材教辅出版,打牢语文教育根基
教材教辅出版是部分出版社业务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教材教辅中先秦出土文献相关内容的比重和分量,既需要专业教材编纂机构和人员的实践与研究,也离不开出版机构的共同呼吁和努力。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对历代形成的古书文本还未形成刻板印象,对新文本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在语文文言文教学中,应加强相关内容的学习。马智忠认为,甲骨文、金文、战国简帛等出土文献是原始的古汉语材料,比传世古籍更能反映古汉语的真实面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与时俱进,吸收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把学术前沿观点纳入教学内容。此外,考古资料对于理解文言字词也能发挥重要作用[5]。
有了专业学者编制的普及性读物出版,语文教育也要主动在教材、教学中充分体现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校订研究成果,让学生初步掌握这种“二重证据”阅读方法,培养其阅读出土文献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除了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点,还可以通过简帛仿制、文字描摹等手段,让学生直观掌握简帛书写的特点,深刻体会这种出土文献的阅读方法。
如何在语文基础教育中突出先秦出土文献的地位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当前的语文教育没有明确区分语言学和文学两大学科体系,通常是以文学为主,兼顾语言学,语言文字更多扮演了“辅助工具”的角色。其实二者的学习研究对象、方法、理念有着明显差异,可以说语言文字是文学的基础。学生欠缺独立的语言文字思维和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会限制其文学阅读、写作、鉴赏能力的发展。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让学生拥有独立的语言文字观,是提升先秦出土文献教学地位的必由之路,也是将来语文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推动先秦出土文献融合出版
一是提升先秦出土文献的材料著录水平。材料著录是刊布、揭示出土文献的首要步骤,著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释读和研究成果。从最早的手摹、墨拓,再到照片、全息影像,直至如今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先秦出土文献的著录始终走在技术的前沿。管文韬先生说:“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时代,甲骨文的著录已经不单单局限在纸质的书页上了。当甲骨文与科技相结合,甲骨文电子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就成为现实。”[6]先秦出土文献的材料著录将不仅限于纸本载体,而与视听影音、多媒体、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读者不仅可以阅读,还可以触摸、体验、感知。这是未来出土文献材料著录的发展趋势,也是出版行业面临的极大挑战。
二是提升工具书编纂出版的数字化水平。工具书包括文字编、文本索引、集释汇编等多种类型,是阅读、研究先秦出土文献的学术利器。当前,诸多学者已认识到利用数字化手段编纂工具书的便利性和重要性,但整体编纂水平有待提高。具体表现为:工具书的出版形式仍以纸质出版物为主,缺乏数字化的统计属性和互联网的关联属性。出版机构应大力开发相关应用程序,促使工具书编纂数字化、自动化,这也有助于工具书使用的便利化和共享化。
三是通过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等手段,打造先秦出土文献的“出版—发行—推广”全流程平台,以此打通文献典藏、整理、出版、阅读、研究等多个环节。出版机构处于典藏研究机构与读者之间的关键节点,是推动建立阅读推广平台的中坚力量,要扮演好桥梁角色,将更多的先秦出土文献通过全流程平台传播出去,将更多的读者流量引入全流程平台的共建共享中。
(四)打造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发行营销模式
一是吸引古文字学、出土文献学等科班人员进入出版业。在出版编辑学等专业课程中,适当增加出土文献相关的选修或必修课,在这些未来有志于从事文献出版工作的人才中播下种子。同时要重视行业内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用好学者资源,让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作用,通过课题合作、专业培训等方式,帮助提升出版行业从业者对先秦出土文献的选题策划、编校发行水平。
二是要努力探索适合先秦出土文献阅读推广的图书发行模式。出土文献类图书专业性强,文化吸引力也强,与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博学、历史学等关系密切,其发行推广模式也应遵循跨学科、跨领域的理念。先秦出土文献是一种十分依赖阅读实践的文献资料,丰富的活动能够引起一部分读者的兴趣。因此,要想方设法将图书发行营销和读者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形式相结合,如举办读书会、分享会、国学启蒙课堂等,扩大先秦出土文献的影响力,提升其受众度。
图书文献以阅读为指归。不断扩大和提升先秦出土文献的出版发行规模和水平,才能促进其阅读推广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只有不断拓展先秦出土文献的阅读推广阵地,才能对相关的文献出版事业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基于当前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并深刻影响着学术史发展这一大背景,可见先秦出土文献的出版空间何其广大。诚如刘钊先生所指出的:“在此建议有能力的出版社要提前布局,尽早‘预流’,争取在出土古籍的出版上占得先机。”[7]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林沄.古文字学简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曹方向.甲骨文读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4]刘钊,冯克坚.甲骨文常用字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9.
[5]马智忠.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大众文艺,2020(19):195-196.
[6]管文韬.珂罗版、大数据、人工智能……甲骨文著录从来都是“高科技”[N].中国青年报,2019-11-19(04).
[7]刘钊.新时代出土古籍的整理、出版与应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7-1(A04).